
鲍德里亚

福柯

萨特

叔本华

尼采
“与现在学科分野林立、甚至一个学科内部流派不同都无法对话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话语,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谈萨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成为一种学术的共相,这种共相不仅是不同学科之间,也在左右之分之间,当时的左派和自由派,谈论的对象也是比较一致的。”
越界
网络搭建青年译介共同体
大学读传播学期间,邹荣在一门媒介批评的课程上接触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等现当代批判理论,便开始对此着迷。2012年,他心理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了重庆大学出版社,又重拾了早年对西方人文思想的热忱,即刻开始探寻出版的思路。
因为资历尚浅,重庆大学出版社在理论译介方面又是新起之秀,难以吸引来有名望的老师,邹荣就开始转投豆瓣网,在上面寻求学术青年的帮助。他在2013年间,一边做“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一边在豆瓣上依循着原版书条目下的阅读者和思想家相关小组的路径,寻找合适的译者。一年来,通过相互推荐,青年译者群的“网络”越来越大。他发现豆瓣上潜藏着一个若隐若现的青年学术共同体,他们有相似的阅读兴趣和学术热忱,只是还没有被凝聚起来浮现在公共视野当中。
邹荣主持的拜德雅系列丛书就把这批青年人网罗了起来,这代人卸掉了前人的历史包袱,又在留学热的背景之下消弭了和西方思想的距离,因此和他们的前辈比起来,便拥有完全不同的视野。在邹荣看来,出版要有前瞻性,除了寻求“名师”光环的庇护外,青年译者和作者的培养也许更重要。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联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那样,他们合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员甘阳、刘小枫、陈嘉映等人日后都成为了学界最有名望的大师。学界在更新换代,而拜德雅在今天网罗的,也许就是未来学界的顶梁柱。
“以往的学术出版往往是依托于学界的老师,老师又经常委托给自己的学生。而我们直接把策划的书单挂在网上,公开招募译者,报名的人几乎都是在读博士,他们试译一部分,过关了就签下来。”邹荣说。有学者曾赞赏拜德雅的运作是对主流学界游戏规则的“挑衅”。
与以往学者们通过期刊杂志或学术研讨班的方式不同,网络社群让学术青年脱离了精神的“孤岛”,匿名环境中的对话与碰撞更及时也更容易产生火花。拜德雅旗下“卡戎文丛”是和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合作的一套丛书。丛书的主编白轻(笔名),也是“泼先生”的执行主编。因为以lightwhite的名字在豆瓣上活跃多年,他在青年理论研究者中也小有名气。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九零后的人大在读博士。他借用笛卡尔“戴着面具前行”来比喻今天活跃在网络上的这一代译介者。他们频繁地在豆瓣网、或微信公众号上以一个“符号身份”发布译文,此时这个身份就不再是一个被年龄、性别所规定的人。
“戴上面具,你可以进入另一片领域,另一套秩序,它相对于现实的网络,自然少了很多的限制,这就是让你觉得创作自如的原因。这里有一个越界的举动,一个溢出的姿态,我想,它或许是‘泼先生’作为动词的‘泼’表达的东西。”
就像拜德雅对学术出版机制的挑衅那样,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的发起人芬雷从2007年创办起便也聚集了一众学院的“反叛者”。这些学院内的青年人不愿受学院体制内以学科为分野、以课题为主导、以师生为共同体的知识生产机制的桎梏,聚集在一起开启了另一种实践——在学院外的知识生产和对学院话语的解构中,进行学术思考、艺术行动和写作。理论的译介在‘泼先生’这个松散的共同体中占有了很重的位置,“绝大多数时候是由个人提供并支撑的,而且没有任何报偿。这也许是青年人剩余精力的无目的耗费,但如此的献出总已经朝向了共同体的交流和共在”,白轻说。然而它期望达成某种更大范围内共识吗?“如果有,限度也会很低,它寻求的不如说的异识,是异质元素相遇并碰撞的可能。这是其生机的所在。”芬雷也赞同,“在现阶段,只有每个共同体提出‘异识’,在未来才有一种‘共识’的可能。”
拜德雅·人文丛书的主编南大哲学系教授蓝江,是拜德雅囊括的这批青年学者的领军者。而蓝江更知名的身份,或许是微博上通过微盘贡献了巨量前沿学术资料的“九月虺”。网络使得学术时代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从书籍难以获取,到电子资料广泛流通。“九月虺”这个账号所分享的原文与译介资料涉猎广泛,立场也不局限于某一个派别。
“在这个九月虺的名字下,有许多的留学海外学子、甚至港台的学者传书给我,让我在平台上可以与大家共享。它早已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分享资料的共同体。”蓝江把他共同参与上传、下载、传播这些电子书籍的行动比作“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资料随着传播和更多人的阅读使其价值得到最大化,成为当代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之时,就像“火种”以其应有的方式留下痕迹。
启蒙
现代化之路上迷途的“西学”
蓝江回忆起他在念书时期的八九十年代,床头总会放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虽然读的不是太懂,总是感觉在萨特的字里行间中涌现出一种让我陶醉的力量。”而隶属于同一套丛书中的另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则让八十年代末期进入中文系,后在九十年代末成为西方当代理论译介领军的汪民安非常兴奋——“很快地让我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教科书产生了厌倦。”在八十年代进入高校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记忆——能买到的书很少,整个社会陷入了对知识的无限焦渴之中。
改革开放在知识界掀起的最大的涟漪,莫过于“西学热”。“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之际,人们被抛入了一个“野蛮社会”。闭关锁国三十年后,学术界更是一片荒漠。对于本土问题的焦虑,知识界开始转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之前的古典哲学的译介,“改革开放前普遍认为‘马克思以后无经典’,于是,从八十年代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中国和西方思想断裂了整一百年”,《读书》杂志前编辑部主任、“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编委王焱回忆到,“1986年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三联书店,就把出版的目光放在了这一百年间的西方思想上。”《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西方人文思想经典相继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
那些书籍在一片荒漠之中无疑起到了“启蒙”作用,为一代人打下了共同的知识基底。“与现在学科分野林立,甚至一个学科内部流派不同都无法对话不一样,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话语,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谈萨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成为一种学术的共相,这种共相不仅是不同学科之间,也在左右之分之间,当时的左派和自由派,谈论的对象也是比较一致的。”蓝江回忆道。
而这一共同知识的基石,便是届时正就读于北大外哲所的甘阳所发起的轰动一时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所打下的。张旭东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中谈及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新启蒙运动”)中的三个流派,也就是当时先后成立的三个编委会: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以讨论“科学”的姿态完成20年代初期在“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帜下未完成的启蒙;汤一介、李泽厚牵头的“中国文化派”企图寻求儒家传统来完成文化重构;而甘阳、刘小枫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则把目光放到了西方现代思想。
甘阳组织的编委会成员从今天看来,大都早已在各自领域中独领风骚:甘阳、刘小枫、刘东、杜小真、李银河、陈嘉映、周国平、赵越胜、徐友渔、钱理群等。他们发源于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在知青文化的余音下,很快就形成了小圈子。他们探讨哲学、谈论诗歌,在高干子弟家开Party。




《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等书在当时成为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年轻人追求时尚的标志。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八十年代访谈录》
三联书店的前总经理沈昌文忆及甘阳的编委会找到三联,本就重视翻译的沈昌文大力支持,甚至违反纪律送给他们一本盖了图章的介绍信。在出版社方唯一在编委会中待过的王焱的记忆中,三联本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开始了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丛书名目,相继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却从未想到那套书销路那么好。
“《存在与时间》发得太火了,发了7万册,《存在与虚无》10万册。这些书当时成了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一个标志。”薛巍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开启学术新思潮和新方法的窗口》中援引了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的回忆。
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人文精神”的热潮之中,而哲学在那时又占据人文学科的统领地位,大学校园中大批的文学青年追着“人文思想”的潮流,似乎理论思想大行其道是很好理解的。然而吊诡的是,正在现代化探寻过程中摸爬滚打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便是反省自身的历史问题和为改革探路。而这套风靡一时的丛书,不但无法为“现代性”指出方向,反而是“反现代性”的。
从尼采到马尔库塞再到海德格尔,这些脱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历史现实中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史,其中最深刻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说,编委会通过译介这套书,在从未切身体会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智识层面却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语境——这个圈子的主流话语是批判资本主义、反现代性的。
编委会的成员之一陈嘉映回忆到,甘阳当时的雄心是“正学术源流”,并未考虑与现实接壤。然而在举国上下反思历史、拥抱西方现代观念的气氛中,“西学”在那个气氛中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也谈及了大众在对思想的空前饥渴中,对他们译介的艰涩的“西学”,在云山雾罩之中产生了阴差阳错的误读:“这批西方人虽然是反西方的哲学,但对中国人来讲,不就是‘反’嘛,还是迎合他们‘反’的情绪。”并且,通过对这套书的阅读,人们习得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的批判语言。”
张旭东把那一批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译介进来的思想称作“漂浮的能指”,它们没有本土的自觉性,仅仅成为了“自在之物”。他在《重访八十年代》一文中写到,“八十年代‘援西入中’的一代人想象中的西方和西学,如今已同商品一道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直接现实的一部分。”
的确,三十年后的今天,身处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与消费时代之中的我们,在切身体会着“现代性”的困境的同时,才有能力从内部理解那一时期精英知识分子们想象中的西方与西学。
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
断裂
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衰落
虽然甘阳编委会的那套丛书不但和本土问题脱节,在当时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背离。但是,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仍然为本土在“话语”上带来很大的变化。一批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以“新的话语”影响了知识界,也为后辈打下了西学的基底。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整套丛书被批判为“全盘西化”。“本是批判西方的,却被指认为‘全盘西化’”,王焱笑道。编委会也因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复杂原因,不欢而散了。解散后,编委会的成员便卸下了早年的“人文情怀”,各自转向了精深的领域。
王焱谈到,“哲学在西方也遇到了危机,统领各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地位动摇了,逐渐地走向了技术化、专业化。”
而在中国语境下,“人文精神”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显得再也不合时宜了,文人纷纷下海经商,抑或躲进了象牙塔。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回忆到,“九十年代后整个世界的变化,东欧剧变,社会政治问题变得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了。人文基本走不下去了。”自由主义思潮随着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兴起,知识界在认识论上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人文精神”在时代中就此落幕了。
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九十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人文失落”的堪忧。“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王晓明在1996年汇编那场讨论的诸多文章所出版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中写道。
借用张旭东的话,“‘八十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
“九十年代前期,西学译介陷入低谷,而台湾正大张旗鼓地译介,主要征召大陆廉价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回忆到,“当时两岸都没有版权制约,我们各自已有一些译作,大陆西学译作市场低迷,我们便与台湾出版商一拍即合。”刘北成等当年已经译完福柯的经典著作《疯癫与文明》,却无处出版,于是签下了台湾的出版社,随即又翻译了《规训与惩罚》,1992年在台湾出版。洪汉鼎对伽达默尔所做的系统的译介,也于1993年被引入台湾。九十年代末期,内地学界开始复苏,刘北成等人的两本福柯译作才被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引入。
复苏后,西学的译介也不再有八十年代共同体的力量,而是单打独斗、各自为营。早年编委会的成员之一杜小真,坚守着八十年代自己对法国思想理论的译介,在这一时期陆续在三联书店主编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同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了《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九十年代末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带着对法国当代理论的热忱,开始加入西方前言思想译介的阵营——主编了“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
“学术生产并不非要形成所谓的共同体,知识的历史就是歧见和争论的历史,孤独的个体同样可以产生了不起的思想。至于我选择的书,完全是按照我的趣味来的,我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就会选择哪方面的书,比如说,我从没有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产生兴趣,我就不会挑选这方面的书。”汪民安说。
2004年开始,汪民安独自主编了《生产》辑刊,每年一期,即刻成了西方思想前沿的风向标,紧密追进西方最热的理论思潮,在国内最早介绍了巴迪欧、阿甘本、生命政治、思辨实在论等。
出版人杨全强在2003年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走上了理论译介的主持工作,随后辗转到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了鲍德里亚、布朗肖和德勒兹的译介。2013年,他转投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启了和汪民安“人文科学译丛”的合作,他们定下了出完100本的长期计划。
拜德雅·卡戎文丛的90后主编白轻回忆到,“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言,对西方前沿理论的接触就是从《生产》开始的,或许还包括更早的‘话语行动译丛’中由汪民安老师编选的《巴塔耶文选》这样的读本。我很难描述初读那些文本和理论带来的震撼,直至今天,它们对我仍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我想,这样的诱惑力也许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献身理论研究的原因。我必须承认,卡戎的工作是在前一代人已经敞开的视野下进行的,没有过去十年二十年搭建起来的框架,现今的任何尝试都难以想象。”




“拜德雅”导读系列丛书为阿尔都塞、德曼、波伏娃、齐泽克、列维纳斯等思想者设计了别致的肖像,他们若隐若现,需要返回他们的思想之中才能重新辨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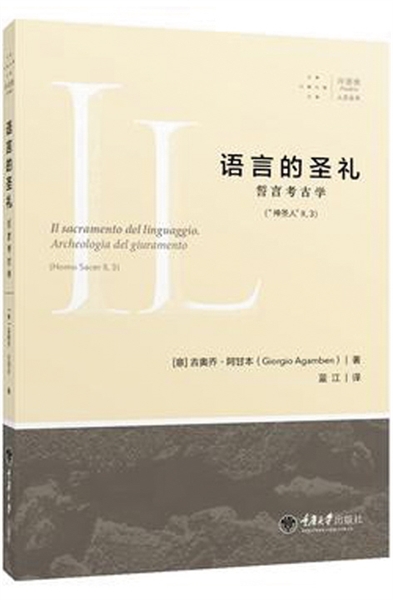
《语言的圣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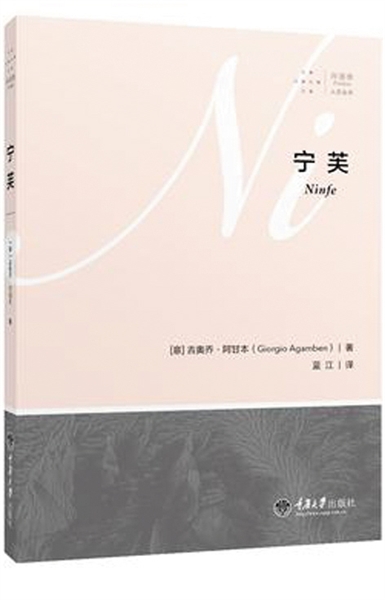
《宁芙》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

《福柯的最后一课》
传承
从学科分野到“人文学科”的重建
近年来,西方理论的译介又迎来了一小波热潮,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以及重庆大学出版社纷纷介入这一领域,围绕着这些主题争夺版权,有时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被几家出版社“瓜分”得七零八落。然而,再也不像八十年代,每一波译介的思潮都能起到洗心革面的作用了,更不要说制造学术上的“共同话语”。
知识界因对现实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愈发难以弥合的鸿沟,政治立场的分化、学科的分野林立,使得“话语”上的共识越来越弱。“大家会援引各自领域的大师,而各个学科之间的译介,也早无这种集体对话的可能。”蓝江感慨道,“今天也涌入了很多思潮,但是现在势力范围划分已定,大家只读自己分片内的书,这个是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地方。”王焱苦笑道,“八十年代的编委会如今若是再聚集在一起,大家恐怕再难就任何事情达成共识了。”
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中许多人丧失了对知识的渴求,思想的深度被逐渐填平。所以说,今天的局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反的,八十年代是思想极度贫乏引起的对西学的渴望,而今天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已经冲淡了思想的味道,让思想和学术本身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信息。人们更喜欢在有用和没用的二分中来审视其中出现的一切信息,比如风水有用,德勒兹没用,周易有用,黑格尔没用。这个结果,本身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症候,将一切有深度的思想贬斥为有用-无用的二分的信息。今天恰恰是书籍众多反而大家不看书的时代。”蓝江说。
“而像巴迪欧、阿甘本这批欧陆当代思想家的译介,就是根本去冲击我们认为有用-没用的那个庸俗的日常划分的东西,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破碎之后,为迷失在海量数据信息的迷宫之中的我们重新找到一个精神的方向,一个可以走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带来的碎片化困境的一个指针。”
出现在西方不同阶段的历史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几乎同时被引进。在经过时间锤炼的西方现代思想的经典已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如饥似渴地引入后,虽然还未被消化殆尽,译介的重点已经放到了当代,尤其是法国当代理论。互联网的平台使得获取文献资料比早年便利太多,大量留学生在西方接触到了前沿思想,开始投入到了译介工作之中,西学的译介也从过去几家独大的权威“导游”,引向今天自下而上的多元民主式实践。
然而,当学术青年一窝蜂赶时髦一样地追着西方最前沿的思想,很多重要的理论家似乎还没热就淡出中国学术界的视野。邹荣也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了理论出版领域——这几年理论界的热闹景象从长远看来是否对于学术生产和相关出版是不利的?但是这几年做下来,他感到“赶时髦”在这一节点上的必然性。“国内这几年一直在追的激进理论,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法国。我们也知道,战后法国思想界确实是人才辈出,就像巴迪欧说的:‘法国哲学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后第三个黄金时代’。事实上,随着上一辈‘大师’的离去,那种‘群星璀璨’的局面已经很难出现了。”在邹荣看来,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理论原产地的学术界的普遍“焦虑”,“我看到国外出版社对于这类书籍的出版也是很‘疯狂’的,所以感觉他们事实上也在参与这样的‘造神’。”
某种程度上,这些理论是上世纪诸多惊人思想的一个余波。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国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这些昔日的荣光下,今天的思想只能算强弩之末,但即便这样,它们也还在迟缓地进行着某种推进。在新的思想到来之前,它们会是一个悠长的回声。”白轻说。
而老一辈的王焱则提醒说,对今天的理论译介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八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不同,今天的书籍首先是商品,要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消费。资本主义系统在今天早已收编了所谓的‘批判’,‘批判’如今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批判得好,市场价值就高。”他把今天的理论热看作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泡沫”,“新出的可能是速朽的,未必代表学术深度。”
在蓝江看来,“今天的翻译十分重视对思想史上的补缺,不是片面追新。比如现在重新对康吉莱姆和西蒙东的著作的翻译,实际上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将法国战后思想史的谱系连接起来,而不是一个个稀松的断点。”作为出版人,邹荣也担心很多今天译介过来的西学成为“过眼烟云”。“出版的一大功能是遴选,选择那些有价值的能够流传下去的内容”,他把“填坑”也作为今天从事出版的一部分责任,以思想的传承作为导向。
前沿理论的译介更大的意义,白轻认为,在于“它们本身就是对西方社会之现实的回击。所以,不论是在课堂,还是在街头,你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在批判意识上,今天的时代无比需要它们。”然而,这一诞生于“西方社会之现实”的最前沿思潮又和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怎样的距离?它们是否带有本土的视阈?会不会又像八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那样,成为张旭东口中“漂浮的能指”?
“我们和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他们感受到的问题我们也能感受到。”汪民安反驳道。
我不认为今天有谁可以主动地躲避现实了,因为现实正向他扑来,无时无刻不在击打着他,迫使他做出反应。有不止一个的现实,每个现实既有直接的需求,也有深层的需求。译介不需要选择朝向哪一个现实,它已经被现实的刀刃挑到了它所知的最残酷的东西面前。”白轻补充说。
“本来当时一位译者朋友跟我提议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欧洲时刻’”,邹荣介绍,“这样做是为了也许有一天可以引出‘中国时刻’。”
最后,蓝江为这套书正式定名为“拜德雅”。他在出版前言中写道,“‘拜德雅’是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用于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它所涉及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提出“拜德雅”这个概念,也是想再学科分野林立、难以形成集体对话的今天,引向某种大的“人文学科”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