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末,笛安的最新小说《景恒街》出版了,距离她上一次出书已经有四年。四年时间里,她在社交媒体平台更新日常动态,留言处总有读者变着花样催更,她总是回复:在写、快了,有时还会带上泪奔的表情。
好在《景恒街》终于出来了,而且很快获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这个奖项在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从2007年起将长篇小说纳入评奖范围。第一届长篇小说奖由麦家《风声》获得,第二届长篇榜首是毕飞宇《推拿》,第三届则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此次获奖,让笛安成为首位问鼎长篇小说奖的80后作家,颁奖词评价这部小说:“不动声色之间可见时代运行轨迹、社会转型风貌与情感结构变迁。”
获奖结果似乎让笛安有些意外。她给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只打及格分。提笔前,她想让自己轻松些,选择写一个爱情故事,这题材听起来够简单通俗了吧?没想到反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填起来费心费力,成果也不尽如人意。
获奖结果也引起了一些异议。当然会有读者不喜欢《景恒街》这部小说,但更多的反对几乎是下意识的质疑:笛安不是青春文学作家吗?她够格吗?

笛安
很多人是通过《最小说》杂志认识笛安的。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这本由郭敬明策划引领的刊物凭借青春文学的话题性与傲人的销量,在出版市场上风头无两,吸引了一批青少年粉丝。这个平台曾聚集了众多人气作者:七堇年、落落、安东尼……其中也包括笛安。2008年,笛安开始在《最小说》上连载长篇小说《西决》,通过郑西决的角度讲述郑家三个堂兄妹的爱恨成长与家族纠葛。这部小说连同之后的《东霓》《南音》,被称为“龙城三部曲”,也一直是笛安最受欢迎的作品。也是在那个时期,她积累了越来越多热爱她的粉丝,有了粉丝对她的昵称:美笛。
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笛安早已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青春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平均年龄偏低,内容大多浅显通俗,贴近市场,在主流文坛上评价不高,“矫情”、“疼痛”、“无病呻吟”是对他们常见的负面印象。
在一众青春文学作家中,笛安往往被认为与众不同。当年《最小说》开始连载《西决》时,主编郭敬明在对笛安才华极尽赞誉之余,还提及《西决》获得了不少传统主流作家的来信夸奖——这对《最小说》来说显然是鲜见的。外界对她常见的评价是:“介于青春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沟通两代文学的桥梁”。这种评价有点微妙,笛安觉得,可能还是她不够好,因为如果真的足够好,就不会被说是桥梁了。不过想了想,她又补充说:“但是即使我不够好,也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笛安的特殊还在于,她是顶着“文二代”的光芒出道的,父母分别是知名作家李锐、蒋韵。早年间,她有点害怕别人每次提她就要说起她父母,后来渐渐习惯了,也就心平气和:“我不能否认那两个人是我父母,总不能说我是捡来的吧?即使是捡来的不也被熏陶了这么多年。”
笛安一直觉得,自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自己就是两个“文青”的小孩。她小时候是跟外公一起生活的,外公是医生,她从小在医院的家属楼里长大,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一天里也就一两个小时。每天傍晚,父母会过来吃饭,帮她检查作业,最多陪她玩一会儿,就回家了。偶尔母亲会跟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代喜欢的书。在儿童时代,笛安只隐隐觉得父母工作和别人不一样,居然不用上班——“太不像话,太不体面了!”后来她发现作协大院里很多叔叔阿姨都不上班,这才心里平衡了一点。

笛安与父亲李锐
成长过程中,笛安并未过早展露什么写作才能,语文作文成绩一直平平。父母希望她好好读书,以后留在高校教学。高考后,她选择赴法留学,读社会学,是她喜欢的社科专业。或许是异国他乡的孤寂无援点燃了她的创作欲,出国第一年,笛安写出短篇小说《姐姐的丛林》,后来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这是她第一次完整写完一部作品。
首篇作品便发表在《收获》上,已经是挺高的起点了,不过那时笛安仍未下决心终身以写作为业——好吧她说她至今也没有这种信念。读完本科后,她继续读社会学硕士,甚至申请到博士生项目,不过入学后又放弃了。“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在学术上没什么天分,仅靠小聪明去做学术是不够的。“于是,数年的社会学积淀化作她创作的养分。
还好,她在写作上还是有些天分的。早期写小说尤其顺利,她几乎是凭着本能下笔。“20岁出头的时候,我只要有一个概念,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篇小说。”但是到了《西决》,她开始觉得吃力,似乎天分已经花光了。“总觉得这样写不对,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人一旦陷入这个状态,就会变得特别焦虑。”
这种艰难感一直持续到最近写作《景恒街》。《景恒街》的前身叫《金镶欲》,最早刊登在2016年的《最小说》上,经过长时间的调整修改,最后保留下来的几乎只剩人物姓名。写作陷入瓶颈的时候,她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苦熬,完全靠自身的意志力。有时候,她跟作为同行的父母说最近写的不是很顺,她父亲就说,好好加油吧。
写长篇小说的过程太枯燥,笛安开始苦中作乐。《景恒街》里面有一个隐藏彩蛋,女主角灵境和同事闲聊时提起一个消失很久的女作家,说她生了个孩子。熟悉笛安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作家当然是她自己。她还写了一个情节:一位准备离职的同事找灵境要她母校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位老师正是笛安很喜欢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这是她特意为偶像安排的出场机会。她需要时不时地逗读者开心一下,也逗自己开心一下。
当年嫌弃父母工作形式“太不像话”的小姑娘长大了,也成了知名作家,小说卖得还很不错。对不少年轻读者来说,笛安不再是“李锐的女儿”,李锐反而成了“笛安的父亲”。这回轮到父亲有“意见”了。李锐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阅历颇丰,插队种过地、在工厂当过工人,在他看来,女儿年纪轻轻二十几岁就光写作不上班,有点不像话。
其实不完全如此。前几年,笛安担任文学杂志《文艺风赏》的主编,和编辑团队一起操作每期的选题制作。不同于写作,做编辑就是一份工作,而且是她不怎么喜欢的工作。“做杂志必须得有价值观和态度,但是小说不一样,小说不能只想着传递价值观。小说的那个世界更丰富,跟做杂志是完全不一样的回路。“有一次,笛安和几个编辑聊天,其他人说觉得做编辑会上瘾,她说她没有,然后就有一点冷场。
近年纸媒愈发萧瑟,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最小说》与《文艺风赏》都已经停刊。笛安回归到纯粹的创作者身份,只不过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当时是成为母亲——她有了一个百般疼爱的女儿。早上,她要早起送小孩去幼儿园,如果要写小说,她需要在女儿睡着后才能集中精神写作,工作时间变成了晚上十点到凌晨两三点。更更重要的是,小女孩的出现让她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与强大——不是作为作家,而是作为一个人。
十年前,笛安觉得十年后她会写得更厉害,但现在觉得并没有成功做到。“我没能成为当初以为自己必将成为的那种作家。”她露出微笑,有些抱歉似的:“问题是,现在的我已经接受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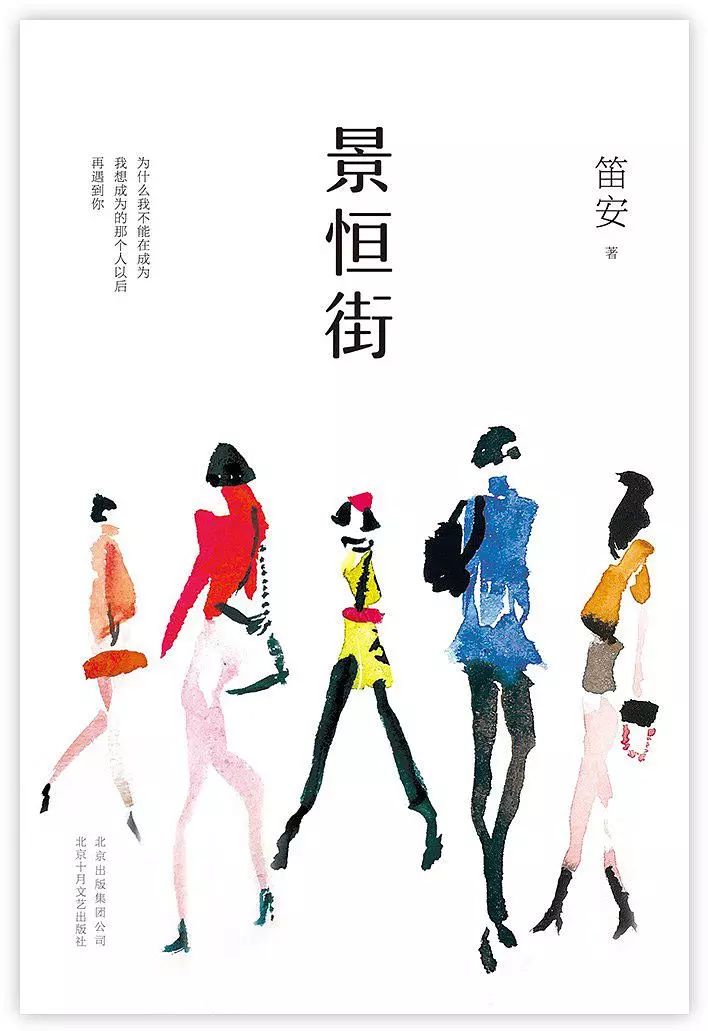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景恒街是北京CBD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
朱灵境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叠”,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他说:“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力。”
Q&A
《景恒街》比“龙城三部曲”难写
凤凰网读书:自己满意《景恒街》吗?如果百分制打多少分?
笛安:在60到70分之间。我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只是我暂时还做不到。我一直不满意小说后三分之一,觉得在最高潮的部分可以再往上推一点,但是体力不支,真的就跟长跑一样。其实这篇小说从一开始进行到最后一直都是困难的。我以前觉得它会很好写,认为就是写两个人谈恋爱,关系从萌生到最后,发展变坏,没有那么难,但后来发现其实不容易。因为爱情故事永远不只有爱情,它肯定有一个外部世界的联络。这两个人之间情感的关系有很多外部世界权力的投影进来,这个转化其实是一个挺微妙的过程。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这次要写一个爱情故事?会不会担心这个题材缺乏新颖度或挑战性?
笛安:我的小说里面真正以爱情为核心叙事的,除了《告别天堂》之外就没了吧。至少按我的标准,其他几部不算是爱情故事。上一部《南方有令秧》其实是一个女人的战争,令秧谈恋爱的部分只有最后一点,只是一个支线,甚至没有参与整个主线叙事。所以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其实《南方有令秧》没有《景恒街》难写,虽然前者的故事发生在明朝,需要做历史背景考究的功课,但只要有了材料,真正成文的过程没有那么困难。《南方有令秧》后面几乎一半的内容,是我生完小孩一个月内写出来的。我这人这点不好,我只有着急了才写得出来,但又总是不着急。前几年我有了一个小孩,把她带到一岁多,开始觉得自己该工作了,当时觉得有理由写一个轻松点的题材,后来发现一点都不轻松,结局就变得很悲剧。
凤凰网读书:书出版后你会主动去搜外界评论吗?我知道很多读者特别喜欢你的龙城三部曲,会不会担心他们对新书失望?
笛安:会搜。其实我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不是说读者必须说我好。无论是说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想听言之有物的讨论。肯定有人觉得失望,有些人更怀念或者更喜欢当年那个笛安,龙城三部曲时代的笛安。但是说实话,我不可能永远是那样,我肯定是会有变化。
其实比起龙城三部曲,《景恒街》这个小说驾驭的东西更复杂。你想,用三本书讲一家人,这个难度上实际上没那么大。虽然每部有主视角的变化,但是本质上来说,讲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悲欢也好,牵绊也好,它的时效性其实没有那么强。我可以发生在今天,可以发生在十年前,可以发生在二十年前,这是家庭关系的属性决定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凤凰网读书:朱灵境和关景恒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小说封面上写着你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你爱它什么?
笛安:我不知道。学生时代结束之后到现在,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和经历,或是人生角色的转换,都是在这个城市完成的。我说深爱可能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个城市里在我人生里刻下了非常重要的印记。其实我没有想过刻意写北京这个城市,我只是想写给自己在北京的岁月。我写了几个在北京的人,还有从外地来漂在北京的人,其实是想写这段时光。
凤凰网读书:我读龙城三部曲,觉得你也没有特别刻意去写龙城这个地方,和乡土情怀或是城市文学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笛安:对,其实我没有刻意地写说龙城必须是哪个城市。我觉得当代中国很多地方,尤其北方,很多中等规模城市的生活差不多,没有不可替代性。我也不是一个很有乡土情怀的人,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凤凰网读书:写《景恒街》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写不出来的话怎么找灵感?
笛安:写不出来就熬,有的时候必须熬。这个时候灵感没有用。就是熬过去,就像最后那个长跑总是有冲刺的阶段一样。如果实在不行,就想一个回避的办法,先写会写的,或者说如果这一场戏里有这几个人,ABCD,先写那个会写的人,从这开始,慢慢慢慢会冲出一条路来。
凤凰网读书:你的写作场合一般在哪?书房吗?
笛安:我没有书房,特别讨厌这个存在。我写东西一般都在自己的床上。我不喜欢在书桌前面坐好那种,特别不喜欢。对我来说写小说是私生活。写完了之后怎么去宣传这本书,是工作,怎么去跟别人解释它,是工作,跟你坐在这儿聊天,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天天跟灵境和小关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私密的一部分。
我会真的心疼每一个角色(剧透预警!)
凤凰网读书:男主角关景恒的创业公司是做一个叫“粉叠”的粉丝追星APP,小说里也有不少关于粉丝与偶像关系的描述。为什么会这么设定?你平时有追星吗?还是说这个题材比较贴合当下热点?
笛安:我本人不追星,有时候会有观察这种现象。我一开始没有想过会那么细致地去写那个“粉叠”,但是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这两个人之间情感的每一步转折,其实都跟“粉叠”是有关的。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粉叠”是他们俩之间情敌一样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情敌的描写态度应该认真一点。
我觉得粉丝与偶像的关系里面有一种梦幻感,因为在外人看来,可能觉得一堆粉丝为一个人攒钱打榜很不真实,所以这个元素放在故事里面有梦幻感。站在我角度想一想,我也可以写男主角去创业送外卖,但如果我写他怎么送外卖,你愿意看吗?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送外卖的江湖也很激烈,也可以写得很好看,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关景恒是一个曾经短暂辉煌过的偶像歌手。其实在书里我没有写得太明白,他在那个短暂走红期间是享受过做明星的瘾的,但是没赚到钱。如果把这话说得太明白,有一点不好看,有一点不得体,就点到为止。事实上关景恒非常渴望世俗的成功,他非常渴望能够脱胎换骨,挣脱自己的出身来历。我一开始就想写一个落寞的选秀歌手,他想要再拼一把,这是男主角最开始的定调。他该做什么来改变命运呢?对他来讲,可能离他近一点的、比较了解的就是粉丝,至少这个回路还是能够成立的。
凤凰网读书:小说很多矛盾点是聚焦在男主角这边,女主角灵境的性格比较克制、平淡,跟你以前写的东霓、天扬这些很有个性的女性角色很不一样,你有意识到这种转换吗?
笛安:对,总体而言灵境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写一个比较温和的女主角。我朋友也说,你的女主角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因为现在我情绪更稳定了,也许跟我做了妈妈有关系。
凤凰网读书:小说结尾突然就发生了一场车祸,我不太喜欢这个安排,读到这里觉得有种被巧合意外硬生生切断的感觉。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收尾?
笛安:不巧合也可以,没有这个车祸其实也可以。我当时想过要不要把这段删掉。如果删掉,男主角的关系依然会这样。我最早的时候设想过,在车祸之后有一段灵境坐在病房外面,等着他被抢救的戏份,她会有一段独白,真的在心里问自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没意思,就没写这段。
现在小说最后也有一段独白,但是真的已经简单了好多。我曾经很会写一个人内心非常大段的独白,这个我的读者都知道,他们也爱看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后来想,我索性不解释了,我试试索性不再解释灵境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灵境为什么没有放弃。其实她不再爱这个人了。我一个朋友问我,最后那些问题是谁在问灵境,是小白龙吗?我当时一想,觉得这个画面还挺可爱的,我朋友觉得是灵境在跟她的车对话,你还爱不爱这个人,你在人生中到底还想要什么……其实她有点回避问题,她自己不想回答。
凤凰网读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哭过吗?
笛安:我自己在具体写作的时候不会哭,从来不会。但是我有真的非常心酸的时候。我会真的心疼每一角色。我为什么对这个小说还是有偏爱?因为有几个地方我写到的时候,真的曾经很难过很难过。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会觉得意外,是写“钢铁侠”的前事。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德州,去买披萨,到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好荒凉,安静到简直像坟场一样。你知道在德州这个真的是非常常见的场景,外面简直是荒芜人烟,有一个店,你进去,其实人都在里面。他买出来了以后,发现停车场还是荒无一人的。他一个人坐在车里,他很想回北京,他觉得再在那待下去自己会死掉。因为我自己在国外待过好多年,我真的有过类似的时刻。我在写他为什么那么坚持想回北京的时候,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曾经的那些东西,我以为我已经忘了,但它们又回来了。
另一个地方是写小关和灵境,他们老板过生日开party的时候,就有人说,你是关景恒本人,你来唱一首歌。他是不愿意的,觉得好像瞬间就被打回原型,当然其实是他自己过度敏感,但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太在意别人怎么对待他。我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觉得他那一瞬间的体验也是很真实的,一下又回到少年时代自己的身体里。最后解围的是灵境,借着一点酒劲,她那个时候想的是你们谁都不可以为难他。我觉得这两个人在那一瞬间都是很无助又很可爱的。我写这些,等于我陪着这一群人走了这一段路,就会有那种非常真实的体验。
凤凰网读书:我印象特别深,你经常写灵境坐在小白龙(她的车)里想心事,尤其是洗车的时候,关上车门,洗车的水洒在窗上,独自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特别真实。这是来自你的个人经历吗?现实生活中如果有心事,你会如何排遣?
笛安:真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会想喝两杯。不用醉。肯定要跟朋友,一个人喝容易醉,而且一个人喝起不到排解的作用。有时候我会在停车场,不下车,在那呆坐一会儿。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吧。我还没驾照的时候,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她每天在自己家楼下停车,会坐半个小时再上去。我当时理解不了,后来有点明白了。可能没那么久,但真的会愿意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车载电台的一首歌还没听完,这首听完了又想下一首是什么。
凤凰网读书:有没有考虑过写的角色哪个最接近你本人?很多人说东霓像你。
笛安: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身边有朋友说其实我把自我埋得非常深,埋在四百年前——其实令秧身上有些地方挺像我的。周围有些朋友这么说,我也觉得有点道理。我少女时代真的是非常懵懂的人,觉得呆萌是一个褒义词,就是特别傻,像令秧一样,不懂一些基本的人情世故。但是令秧她没有坏心,而且她的傻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种。我在写令秧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可能我小时候就那样。她确实是不懂,她就问,还不知道自己在闹笑话。比如小说里有一段,她的继子跟蕙娘聊天,继子其实比她年龄还大一点,蕙娘又是个人精,两个人在聊朝廷的事,聊东陵党、阉党这些。令秧听见了,说,这个有什么难的,让皇上杀头不就完了。她的继子就用成年人的思维跟她说,皇上哪能随随便便把满朝文武的头都杀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她说,为什么不是?我小时候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我在写这些地方,写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的时候,就借旁人的口说:“夫人,您就是爱说笑话。”其实她就是那么想的。

笛安
人类对故事的需求是永恒的
凤凰网读书:你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有自信,觉得可以以写作为终身事业?
笛安:我到现在也没觉得它会是终身事业。只不过当时《西决》卖得好了之后,我开始写《东霓》的时候,发现《西决》那一年赚的钱好像够我活几年。我回北京,可以付几年房租,可以一个人生活、吃饭、买衣服。当时就想暂时钱够了,也没多少,但是够我自己生活了。然后就决定先什么都不做,去全职写两年。当时其实我爸爸希望我有地方上班,他一直都认为年轻人应该有一份工作。
在写作方面,我算是运气不错,但是其实写龙城三部曲那几年是我最痛苦的瓶颈期,当时我跟人说也没人相信,大家都觉得我没事找事,无病呻吟。所以我就不跟人说了。在《西决》之前,写作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从龙城三部曲开始我就觉得不容易了,越来越不容易,真的是痛苦比快乐要多。写《令秧》和这个小说,有的时候可能读着就三四句话,背后写得很辛苦,真的是熬过来的。
凤凰网读书: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写?意义是什么?
笛安:它还是有成就感了,当你经过了这些痛苦,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而且你会迷恋那种构筑一个故事的感觉。一个结构搭起来,可以顺利推进,这个过程让我觉得是快乐的。而且,虽然说写小说有时让我痛苦多于快乐,但是相对我还是擅长做这个。真的,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个废柴,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
凤凰网读书:所以比起其他文体,你最喜欢写小说?我挺喜欢你的散文,像早年写的《灰姑娘的南瓜车》那些。
笛安:那种是约稿的时候才会写。我特别不喜欢写散文,我不爱写自己的事,不喜欢谈论自己。可能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会自我膨胀,很有表达自己的欲望,但是我的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写散文是一种对自我的矫饰,或多或少。我不太愿意每天花时间去干这种事。
凤凰网读书:之前你在最世文化的时候,会和郭敬明或者其他作者探讨写作吗?
笛安:我们那时候不怎么交流写作,最多互相叫一叫:“写不出来,能不能不交稿”,然后说点别的。其实写作的人之间需要非常的契机,才能去讲自己具体怎么写。因为这个本身很难言传。而且像我现在,年纪再大一点,作家们之间开会,一饭桌坐满了作家,没有人会掏心窝说我写作最近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后来听一个人讲,像我这样随时承认自己写不出来的人其实都不太多。
凤凰网读书:有一种常见的评价,说你的作品介于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你对此有什么感想?当初在《最小说》上连载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说你跟其他作者写得不太一样,不是那种纯青春文学。
笛安:我也没什么感想,别人愿意怎么说都行,但我自己没有那么想过。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是以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在对待自己的作品。他写出来算什么文学,有的时候作者自己并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这小说就是年轻人写的,就是年轻人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写青春文学这个类别。其实我年轻气盛的时候会有一点不服,《麦田守望者》是不是青春文学?塞林格写的是不是青春文学?就因为他用英语写,他是美国人,你们就觉得他是通过写青少年的困境来揭示人类的困境。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也就是说可能还是我不够好。如果你再好一点,就没有人说你是桥梁了。但是我唯一只是觉得即使我不够好,也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当然现在想开了,这些都无所谓。
我没想过要去靠近严肃文学。可能有人说《南方有令秧》有点偏向,那是因为它写了一个明朝女性主义的题材。我觉得它容易被评论界接受,真的跟题材有关系。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即使选了一个看着就很学院的题材,也可能完成得非常糟。我更在意每个作品的完成度,因为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我做过区分,我觉得有些作家的写作是文人性质的写作,他们读过很多书,有非常深厚的修养,确实对很多事情都能发表观点。文人写作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很多的作家——我不好说是谁——我认为他们首先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写小说也好,写诗歌也好,是文以载道、托物言志,这些都是为他们知识分子身份服务的,是有这么一种文人写作。但我不是。我个人对写作的认知和态度,偏向像莫言老师说的:“你首先是一个手艺人”。写小说首先是有技法的,你得先承认这件事,才能有进步。故事本身有方法论,当然小说不等同于故事,编故事有编故事的章法,写小说有写小说的章法,写小说的章法大于编故事的变法,但这两套技法你都得学。学会了我们再谈其他,我们再谈境界。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思想跟技法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有时候有轻视技术的传统,但说实话,什么叫“鬼斧神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境界到了某个程度,和技法交融在一起,有非常美的东西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很低产,但是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职业化写作的作家。
凤凰网读书: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起写什么,你更在意怎么写?
笛安:我更在意为什么要写,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无所谓。当然我们评判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去评判这个人的动机,犯罪才要讲动机。你为什么要写,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但是评价作品有时候不能不管这些,我们要看你完成得好不好、在这个框架里面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没有、有没有做到非常张弛有度的表达。这是评判的一些标准。对我来说,写作曾经是为了自我表达,后来就是为写作这件事了。有点像建筑所说的营造法式。现阶段的写作,我是愿意去探究这个东西的。我能做的还是尽可能地写一本好小说,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变过。
凤凰网读书:你想过写小说会承担一种什么社会功能吗?有人提出说这个世纪小说将走向终结。以前的小说家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才,需要懂很多东西,能够科普很多知识给读者,但是随着书本分类增加、科技工具普及,小说这部分功能已经开始消散了。当代读者为什么还需要读小说?
笛安:我觉得,除了极少数真的是对文学有挺深的热爱的,绝大多数读者看小说还是要看故事。我认为写小说,作者跟读者之间真正能够产生交集的那个区间还是故事,但是小说本身肯定不能完全等同于故事。从一个现实层面上来说,小说家还是得拥有讲故事的能力。你可以不用,可以说我今天就是不想讲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技能你最好掌握。大家对故事的需求是永恒的。我认为人类需要故事就跟人类当年需要火是一样的。无论讲故事的媒介有多少变化,曾经是戏剧,后来变成电视电影。60年代美国就有人说电影会不会完蛋了,事实证明,目前还没有。
为什么人类永远需要故事?很有意思,这是人类身上有灵的地方。我觉得故事首先本质是符号化的引喻。比如说我女儿——观察一个小朋友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她那时候两岁,看到一个蜡笔画的乱七八糟的红色圆圈,她就指着说“太阳”。一个两岁的孩子,没有人特别给她科普过这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有一种把他见到的、体会到的现实经验去符号化的本能。人类只要拥有这种本能,他就需要故事,因为他需要那个符号化的东西去表达他在现实世界里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投射精神需求也好,情感也好。人类对于引喻的需求其实是个挺神秘的东西,而且绝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凤凰网读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模仿的对象吗?你喜欢的作家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笛安:我一直没有刻意模仿过任何人。不过可能我少年时代阅读过的一些作家,潜移默化影响了我,不叫模仿,而是教会了我一些事。比如说张爱玲和纳博科夫。在我当时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纳博科夫他教会了我很重要的东西。《洛丽塔》的技巧是完美的,把看起来其实有碍观瞻的一件事,做到了非常干净利落的表达。张爱玲她的写法写长篇是有问题的。我到很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她长篇小说少的原因。她没去美国之前,写的长篇都是写着写着自己就腰斩了。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她那个写法写长篇本身就有问题。比如说她非常擅长描绘一个特别具体的场景,和特别具体的对话。一些大的情节的波折她都在这些小的场景里面做推动、做解释,这个写中短篇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说实话,她的这一套对我还是挺重要的,包括《金锁记》《色戒》这些小说,我懵懂期间看得比较多,教会了我很多处理场景的办法。但是在需要处理长篇小说时空的时候,它是有问题的,不够简洁。说实话,为什么长篇小说迷人?处理情节架构、处理人物,还有在人物的关系里推进情节,这些只是讲好一个故事的第一层。还有另一层,是长篇小说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时间。你要处理时间。空间其实没有时间那么重要,现代人的观赏习惯可以接受空间的切换,但是时间是一个挺难处理的变量,这也是长篇小说迷人的地方。
凤凰网读书: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跟哪位作家面对面聊天?古今中外、去世的在世的都行。
笛安:马尔克斯,我觉得他会很好玩。我觉得他的散文写得都好好玩,就写他自己。我看过一篇,写的是他一个好朋友过70岁生日,他说祝酒辞,被人记录下来,讲的是马尔克斯在写《百年孤独》期间,有个很闲的朋友每天跑到他家里,问他最近写什么,写到哪了,要他讲讲。马尔克斯不想给他讲《百年孤独》,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编了一个故事,骗朋友说自己在写什么什么。这个朋友到外面奔走相告,告诉一大堆人马尔克斯最近在写什么,把他听到的的给大家再讲一遍。每天如此,变成马尔克斯每天要给他编一个新的故事,回家再写真正的《百年孤独》。这件事可能多少有点夸张,但应该是发生过的。最后《百年孤独》出书了,这个朋友发现内容跟自己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气得一段时间不理马尔克斯。但是后来,你看,肯定很快冰释前嫌。他们在很欢乐地在庆祝他70岁的生日,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在讲。我觉得马尔克斯应该是一个懂得在生活里找乐趣的一个人,而不像有些作家总是苦大仇深的。我肯定想和马尔克斯这样的人做朋友。
凤凰网读书:写作十多年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笛安:我越来越觉作品应该离我个人远一点。作者的ego真的要尽可能地撤离自己的小说,尽可能地远一点。如果一个人写了一辈子,觉得写小说的任务是表达自我,我觉得那挺遗憾的。一个好的作品里包含了特别多的东西,你的自我真的不那么重要,你不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即使你非常特别,也用不着每一本书都在表达你的特别,没有意思。有些作家是这样,但我不是的。这个可能是跟初期很大的区别,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都是为了满足表达欲,对世界有看法,急着抒发,都是年轻。
凤凰网读书:有没有构思接下来准备写什么?
笛安:不知道。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故事,要真的把它写完了,可能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生涯就可以结束了。六七年前就有这个构思,但是一直没有成熟,我觉得我现在写不好。
END
2018年12月,作家冯骥才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近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冯骥才继《义和拳》《神灯前传》后又一部长篇。 19世纪,天津是东西方最早冲突的地方之一
2018年还有20多天就将过去,年终岁尾,国内文坛终于等来了几部重量级长篇小说。它们的到来,既为2018年的长篇小说出版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也预示着明年到来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激烈争夺即将展开。
“高兴死了!”10月26日,著名媒体人、出版人洪晃在自己微博透露新书《张大小姐》出版上市,好友谭卓、姚晨更是转发支持,引来大批网友讨论和围观,刚推出24小时即登当当网小说热卖榜单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