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开满刺桐花的小城,曾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别称为“刺桐港”。那时,它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在经历了辉煌的“泉州时代”之后,明代海路封闭,泉州港迎来了致命一击,从此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在泉州申遗成功之时,我们特邀学者何书彬撰文,呈现了泉州历史上的这段高光时刻,探寻海洋文明发展史上的东方色彩。
作者 | 何书彬
01
旅行家的“刺桐印象”
元朝初年,马可·波罗游历了泉州,通过游记,把“刺桐印象”带回了欧洲。
他写道 :“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蛮子省的各地出售。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微乎其微,恐怕还不到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除了港口规模之宏大,马可波罗还在泉州一带,看到了一幅那个时代的国际化图景。
德化的瓷器正在按照国外的订单成批地生产,它们物美价廉,用一个威尼斯银币就能买到8个瓷杯;埃及人带来了白糖生产技术,使得永春成为了一个热闹的糖业中心;在泉州的街市上,文身师技艺精湛,有许多人特意从印度来到这里文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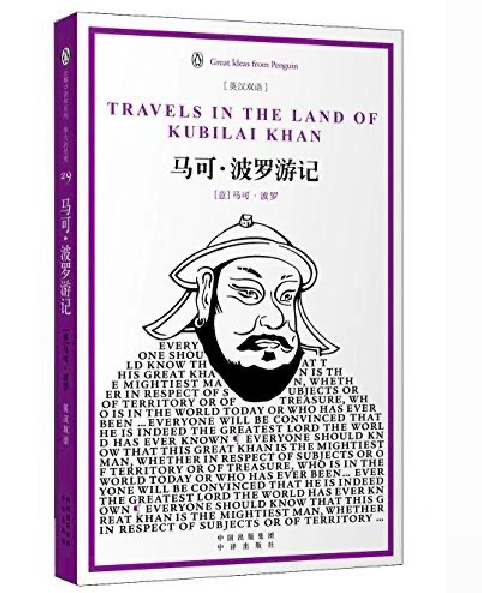
《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 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年3月版
在马可·波罗之后的几十年里,来到泉州的,还有同为旅行家的伊本·白图泰,以及罗马教皇派遣到泉州的主教安德烈·佩鲁贾。
伊本·白图泰写道:“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
他还在印度洋沿岸发现,来来往往的多数是中国船只,其中有些大型中国海船高达4层,在船上工作的海员多达上千人。这些大海船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泉州制造并出洋的。
安德烈·佩鲁贾在寄回欧洲的信里,由于身份的原因,着重提及了当时泉州的宗教情形。他写道,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在刺桐城里捐资修建了一座大教堂,还捐资维持教堂的开支。他说,他作为传教士,可以在这里自由传道,这座城市里还居住着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侨民,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信仰,比如有不少犹太人生活在泉州,他们一直信仰着犹太教。
与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不同,安德烈·佩鲁贾不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1332年,安德烈·佩鲁贾在泉州去世并葬在泉州。他的墓碑如今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并曾在1992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上展出。
02
曾有一个“泉州时代”
马可·波罗等人,是在泉州港的鼎盛时代来到这座港市的。
由于泉州在宋元时期的重要性,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台湾学者李东华,以“泉州时代”,来指代中国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史。
1087年,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开端。这一年,北宋在泉州设立了管理海洋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相当于现代的海关。
这标志着泉州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它走向极盛的转折点。
在什么时候泉州超过了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一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北宋末年,泉州港的贸易量已经和广州港不相上下,而完全取代广州港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则是在宋末元初;第二种说法认为,到南宋初年,泉州港的贸易量才与广州相当,到了元代,泉州港才超过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以上两种说法,虽在泉州港取代广州港的时间点上存在差异,但都认为泉州港在宋元时代的中国,是最具代表的海港。
而且,泉州港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其意义不亚于港口之间的地位更替。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 / 梁赤民 / 董书慧 / 王昶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https://img0.utuku.imgcdc.com/596x0/culture/20210727/739429b4-69de-4af3-be9d-6a8e77302cb0.png)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 / 梁赤民 / 董书慧 / 王昶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泉州港既然在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跃居中国最大港的地位,那么它在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枢纽地位显而易见。因此,当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见到泉州港时,无怪乎他们发出那样的惊叹。
通常来说,一个海港要成为超级贸易枢纽,往往需要广阔的腹地作为支撑,比如秦汉以来的广州港,又比如在近代崛起的上海港,它们都有着巨大的辐射范围。
相较之下,泉州港的崛起,像是一个奇迹。它是如何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呢?
在中国的古港中,泉州港其实是一个后起之秀。在南朝梁代之前,泉州港不见于史籍记载。在秦汉时期,今泉州一带甚至是中原人士眼中的蛮荒之地。
而且,打开地图,我们就可以发现,福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这种地理特征,使得福建在现代铁路、公路兴建之前,与各地的交通都极为不便。这也导致,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中,福建是开发很晚的一个。
一直到晋代,由于中原战乱,衣冠南渡,福建才迎来第一次移民高峰。在此之前,秦统一中国时,秦军并没有进入福建,秦始皇只是在今福建一带设立了名义上的闽中郡,不是指派郡守治理而是由当地的部族首领继续治理。汉武帝时,朝廷指派的军队第一次进入了福建,但汉武帝的做法是“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这就使得,福建曾长期游离于外,汉人对福建的开发,不仅晚于今辽宁、两广,甚至晚于大西南的云南和大西北的新疆。
唐末至五代,由于北方的战乱,福建迎来了第二次移民高峰。人口的激增,以及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福建后来居上,泉州也开始成为一处重要的海港。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前馆长王连茂认为,对泉州而言,公元1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吉祥的世纪”。在这一时期,北方虽战乱频仍,但泉州成功地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泉州港的崛起,与那时中国经济版图从北到南的整体位移这一趋势,是一致的。
北宋时,朝廷设市舶司于泉州,可以说是对泉州港贸易地位的追认。
如果仅仅得益于这个整体环境的变化,泉州尚不足以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毕竟,这种整体环境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广州等港口。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失去了大片疆土后,宋室也失去了大量的税收,急需通过海税来弥补亏空。如宋高宗赵构所言:“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开始着力提升泉州港的重要性。它被选中的的一大原因在于,泉州恰好处于南宋海岸线的中间位置,距离杭州比广州近,距离前来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商人,又较宁波为近。
泉州港也满足了南宋朝廷的期望。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的税收增加了5倍,达到每年近百万缗,占到了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这是属于泉州港的高光时期,也是属于整个福建的一个繁盛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冀朝鼎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
经济学家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统计,在两宋时期,浙江一带兴修水利302次,广东为44次, 福建则多达402次。在农业这个基础之上,那时的福建,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以及茶业、瓷业、冶炼业和造船业等多个产业的中心。
在文教方面,那时的福建也一枝独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出生在福建,治学、讲学在福建,另据美国汉学家贾志扬(John W.Chaffee)统计,两宋进士共有28933名,其中福建路(今福建)的进士为7144名,约占全国总数的24.7%。这一数字,远超排名第二的浙东路(今浙江大部)4858名,以及排名第三的江南西路(今江西)3861名。
不过,在繁盛的另一面,则是沉重的税负、劳役带给民众的巨大压力。两宋时期,福建官员多次向朝廷报告一个现象,由于在税负、劳役之下无力养育子女,福建民众“生子多不举”,也就是在生下孩子后溺婴、弃婴。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朝廷下诏: “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 给常平米一石、钱一贯, 助其养助。”意思是说,朝廷开始发放生育津贴,以应对频发的人伦惨剧。
宋末元初,泉州港虽经历了战乱,但得益于元代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泉州港不但从战乱中恢复,而且保持了繁盛之势。
到了明初,泉州港迎来了致命一击。
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他认为:“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
海路就此闭门,泉州港也在日复一日的淤塞中,彻底地从历史中消失了。

泉南佛国”石刻(《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作者王铭铭摄于2004年)
03
重新发现“刺桐港”
当泉州港退场的时候,它在欧洲却成了一个传奇。
大航海家哥伦布曾经很认真地研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去繁华的“刺桐港”带回财富,是他远航的一大动力。结果是他发现了美洲却误以为就要到泉州了,而且写下日记:“很肯定,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陆了,离刺桐和京师一百里格(注:一种长度单位,约为5.556千米)上下。”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说:“16世纪流行的这样一个词可以让人记起刺桐曾经的辉煌:第一时期的西南季风当时被称为mavsin-i(Zăītūnī),即‘刺桐季风’。”
在15世纪、16世纪之交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掀起了第一场全球化的浪潮。明末,朝廷迫于时势,开放了位于漳州九龙江入海口内的月港,此后由于月港湾多水浅等原因,位于九龙江入海口外的厦门港迅速崛起,成为福建最大的海港。来自美洲的白银,如流水一样通过月港、厦门港涌入中国,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从月港、厦门港运往东南亚再转运到欧洲,在欧洲引起了一场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但是,明清两代,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失去了“东方大港”地位的泉州港,往日光辉也逐渐无人提起,甚至,它被人们普遍地遗忘了。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围绕一个话题争论不休:“刺桐港”在哪里?
这时,马可·波罗笔下那个富庶、美丽、如神话般存在的“刺桐港”,已经成了一个谜。
很多学者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投入这场论争。有人认为,刺桐港指出的是泉州港;有人认为,应该指的是漳州月港,还有人认为,应该指的是扬州或者杭州。
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一直到一百年前,谜底才得以揭开。

刺桐,泉州市的市花(图片来自纪录片《重返刺桐城》)
当时,日本学者桑原陟藏的名作《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问世。他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指出“Zaitun 为中国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
1926年,厦门大学的学者张星烺、陈万里等人前往泉州,考察文物古迹。他们均认同桑原陟藏的说法。
1935年,时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的汉学家艾克(G.EcKe),与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的汉学家戴密微(P.Demieville),合著了研究泉州开元寺东西塔的著作,题为《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由哈佛大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2 卷出版。
1956年,可证明“刺桐港”即是泉州港的实物证据——艾哈玛德墓碑在泉州被发现。墓主的孩子阿含抹用阿拉伯文清晰地记载,其父“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显示其先人娶了泉州女子为妻,并在泉州繁衍生息。至此,“刺桐港”在哪里这一迷雾,彻底拨开了。
如今,刺桐树在泉州里,处处可见,这是一种生长得十分热烈的植物,花开似火,明艳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