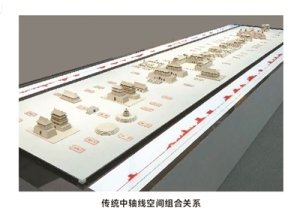布达佩斯大饭店:在童话般的胶片语言里完成电影的自我祭奠
原标题:在《布达佩斯大饭店》里,我们还相信胶片时代的童话

《法兰西特派》
近日,戛纳国际电影节终于公布了2020年,也就是第73届的入围名单。
与以往不同,2020年戛纳公布的片单并未按照以往的传统单元进行划分,而是直接选出了56部影片,并为这些影片统一贴上“戛纳官方入围”标志。
算起来,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这是自1939年以来戛纳历史上第二次停办。尽管已经有很多热门影片选择了转投2021年戛纳,但我们依然能够在2020年的片单里找到一些大家期待已久的影片,比如原定为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片的《法兰西特派》。
从这部影片的预告中,依然可以看到韦斯·安德森的轴对称扁平风格,依然是众星云集,依然穿插着熟悉的默片表演方式,依然在多种屏幕画幅之间切换……
里面的无数元素都让人想起上映于6年前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当时,胶片电影宣告退幕,正值整个行业历史性的沉重转型,很多导演都为此拍摄了讲述电影的电影,韦斯·安德森也在这部粉红色的“童话故事”里记录了属于20世纪胶片电影的回声。
也正如同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在发布2020年入围名单时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在不断演化的世界,不论是观影的方式还是影片本身。受惠于制作电影,给电影生命,接受电影,给电影以荣耀的人们,电影得以对世界做出一些改变。”
《布达佩斯大饭店》,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熟悉到不用介绍了。因为这是很少有的一部真正达到雅俗共赏、在全球范围之内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在世界电影史上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很明确地把自己坐落在了那个数码取代胶片、成为电影的基本介质的重要历史时刻。
2011年,柯达胶片公司正式地退出了好莱坞电影业;2012年,好莱坞本土关闭了最后一个胶片洗印厂,标志着胶片电影这个辉煌时代的终结。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终结的到来,在世界影坛上曾经涌动过一个小小的电影潮流,像是一种电影自我祭奠的仪式。
在2012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片目当中,就包含了《雨果》《大艺术家》《与梦露共处的一周》这样的关于电影的电影。

《雨果》
用文学的说法,我们说这是一个临渊回眸:在电影产业即将面临一个陌生的世界,开始回首百年世界电影史的时刻。
而韦斯·安德森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当中,他选取了一个更有原创性的,或者说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完成电影的自我祭奠,用幽默的、又极端个性化的方式来标识新时代的莅临。
属于胶片时代的二维童话
其实从《月升王国》开始,韦斯·安德森就有意识的在给真人电影赋予一种强烈的卡通感,赋予一种强烈的两维画面的童话特质。
据说《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在匈牙利寻找到了一座老的百货大楼作为它造型的主要参照,但是除了在很少的镜头里出现了那座百货大楼的外观之外,其他的所有的的场景都是由影片的美工师,也就是《月升王国》和《为奴十二载》的美工师绘制完成的。

但是最有趣的不在于这个景是搭的、这个景是画的、这个景是虚的,而是影片当中韦斯·安德森刻意地避免了比如说光给景物造成的阴影,比如说各种各样常规技巧所赋予画面的真实感。
相反,它一直在凸显影片中扁平的、两维的特征。我们会看到山上索道的画面里,全都采取正面水平机位,也就是早期电影的乐队指挥机位,来强化画面的扁平感,而不是去构造画面第三维度纵深的那种虚幻。

这是电影史的参照,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参照。
因为全球电影市场应对胶片电影死亡的办法是使用3D电影,用最强的、最有力的、最直观的第三维度的幻觉,来尝试发掘数码电影的可能性。
而韦斯·安德森反其道而行之,这个鬼才非但不去寻找第三维度的幻觉,相反他充分地让我们去体认胶片时代的电影,其实只是一个两维平面上的“绘画”。所以他使用正面水平机位,使用扁平的景片,使用均匀的布光,使用极端艳丽的单一色调来强化这种扁平感。

同时从《月升王国》开始他就开始大量使用过墙镜头,让摄影机穿墙而过。尽管大家都知道在电影拍摄当中,摄影棚里的每一面墙都是可以拆掉的,但是通常常规电影会选择强化真实封闭空间里的幻觉,韦斯·安德森刚好想要拆穿这一点。

同样,《布达佩斯大饭店》还大量地出现了平移镜头。我们说尽管“推拉摇移”是电影摄影机运动的基本方式,但是“移”这种方式是绝少被使用的,因为平移运动暴露了摄影机的机械特性,以至于它不能够伪装成人眼观察世界的方式。

而韦斯·安德森却把平移镜头变成了他影片当中的一个风格化的元素,再没有什么能比平移镜头更清晰地强化这种扁平感了,他刚好是用扁平感来完成对于电影媒介,尤其是胶片媒介的一个强有力的制止。
所以我们说叫做回到电影自身,它不是在讲述电影史上的故事,而是把这个媒介转换的时刻放回到媒介自身里面去。
当然必须要谈到的是在这部电影中,导演采取的最重要的媒介自指方式,是第一次有人在一部影片当中同时使用了三种画幅规格。
里面出现的画幅规格分别是4:3黄金分割法的经典银幕、16:9的遮幅宽银幕和全幅宽银幕三种银幕尺幅,每一种银幕尺幅对应着一个电影的时代。



而韦斯·安德森的有趣,或者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重要,正在于这部电影始终在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重角色是他再现、他自指、他调侃,他致敬胶片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电影媒介特质。
同时他也向我们展示,数码电影可能完成的魔术与奇迹,例如不同三种尺幅的同时出现。如果是在胶片时代,我们不可能在一部影片当中使用不同的尺幅,它必须在第一个时刻确认并贯穿始终。
只有在数码时代,我们才能完成这样奇特的、不同时代的电影基本形态的同时使用,它向我们标示了电影史的不同时代,也向我们指称这与电影史相关的20世纪的不同时代。
从嵌套结构凝视观众
影片所采取的向世界电影史致敬的方式其实不止于此。大家记得电影的开始,一个小姑娘拿着一本书走进风雪墓园,站在一个作家的墓碑前,姑娘坐在墓地的长椅上打开书,镜头切换为书的封面,封面上是作者的照片,镜头切换为作者的肖像,然后照片转为彩色。



我们进入到了裘德·洛所扮演的作家面对着摄影机的发言,可能是一次采访,可能是自己试图录制一个视频。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导演选择用直面摄影机来反指故事片里,人物绝不直面摄影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定。
在电影表演中一个大禁忌就是不能看向镜头,因为只有演员永远不望向镜头,才能保有整个电影叙事空间的封闭性,才能保有电影世界的完整神秘和观众观影时的幻觉。而在这里,它刚好是用这种打破来自指故事片的规定。
同时大家注意到,韦斯·安德森不仅是幽默的,同时是非常精细的。他故意用了一个可能是作家小孙子的男孩闯进画面,被骂走,然后他再溜回来,把自己置身在镜头当中。


这个小小的喜剧性的插曲在提示着画框的存在,告诉我们是画框这个东西切割了一幕世界,它是画面的起点,也是画面的终点。
那么当作家直视着我们讲述写作的秘密,镜头切换为同样正面水平机位当中的虚构世界里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我们看到作家在和大堂的服务员对话,而后在他的视野当中引出了电影中的叙事人穆斯塔法。同样在正面水平机位的这样的画面当中,电影中的作家和电影中的叙事人面对面,镜头切换为穆斯塔法的近景镜头,穆斯塔法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故事,引出正面水平机位当中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古斯塔夫。



它是用这样的一个视觉的结构来完成了对于19世纪式的经典的,关于故事人物叙事人的一个呈现过程。
有一个公认的说法,说20世纪是电影艺术取代了19世纪的长篇小说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功能,电影成了20世纪的说书人。
所以这个嵌套式的叙事结构、带有玩笑性的镜头段落,同时构成了一个对于经典电影叙事的致敬,或者对于经典电影叙事的调侃,同时它给了影片一个完整自洽的叙事结构。
电影用墓园里姑娘打开书开启故事,用墓园中姑娘读到了最后一页,合上书作为结束。

当然我们如果引申,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完成了一个韦斯·安德森式的经历:用一个喜剧表演式的形式告诉你说,这是假的,这是虚构的,你们只是听了一个迷人的故事而已。
童话式的默片中,隐喻20世纪的历史
同样在这个关于电影的电影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趣的、非常奇妙的结构化的风格语言,在电影当中整个的表演风格是极度夸张的,是喜剧化的,其实准确的说,是默片化的。
所以包括整个演员的造型风格、演员的表演风格,调度本身都是对于世界电影的开端——就是默片电影的一个自指,也是某种反讽或者致敬。
影片里越狱那一整场戏,一直是把玩笑开得十足。他们开始在对话中说,下面有多厚的花岗岩,我们可以挖通它。说来说去等到真的越狱发生的时候,他们其实只不过是挖通了他们牢房的地板,在看守的头顶跳跃,在看守的休息室或者床铺上穿行,所有的这种场景是经典的默片桥段。

所以我们大概很难把它真的联系到比如说我们将要在电影史的时刻当中分享的、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去描述越狱的那样的场景,这是十足的、夸张的、调侃式的一个越狱表演。
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卡通感与童话感,也是通过影片不试图隐藏起电影的虚拟性,而是不断的暴露电影的虚拟性来完成的。
特别典型的一个情节就是古斯塔夫从监狱当中脱身而出,第一件事是要香水,两个人在大风雪当中穿着单衣穿行。

所有这些作为现实主义的叙事元素必须考虑的东西,导演都刻意地把它忽略掉,让我们充分感受到这是一个虚拟故事,甚至只是从前那样的一个童话。
《布达佩斯大饭店》从某种意义上说,汇聚了欧洲影坛属于不同的电影史时刻的大明星和大演员。甚至达到了真正的配角一闪而过的面孔,都是大明星的程度。

但同时导演在试图从剧作、表演、情节等方面把每一个人物都有意识地扁平化,用大家更熟悉的说法就是脸谱化。
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威廉·达福所扮演的冷血杀手,那个冷血杀手的每一个造型元素都在告诉我们,我是冷血杀手,他用这样的东西来达到一种卡通人物似的效果。这部分是构成影片的最直观的、最表层的卡通的和喜剧的元素。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韦斯·安德森的奇迹在于,他使得每一个元素都是精心建构的,每一个元素都是高度风格化的。而每一个高度风格化和个性化的元素,不仅仅是作为作者电影要反身指向韦斯·安德森自身,更重要的是指向他电影的两个重要的诉求。
韦斯·安德森站在电影史转折的时刻,试图用自己的电影来标识它。而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在一个看上去非常童话式的、充满装饰性的美丽影片中,去浓缩20世纪的历史。
我们记得两场火车上的遭遇,第一次在火车上遭遇了军人,以不无温情的、不无喜剧性的幽默场景而告结束。第二次在火车上遭遇了军人,却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这两次火车上的遭遇可以说是两场世界大战的隐喻,第一场世界大战当中旧世界的辉光犹在,而第二场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世界乃至西方文明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毁。
韦斯·安德森反复说,关于这部电影如果有所谓主题,它的主题是:远处的喜剧,就是近处的悲剧。而实际上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许可以做一个相反的理解:近处的喜剧就是远处的悲剧。
因为整个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喜剧性的场景,而喜剧性的氛围或者说幽默的基调掩盖了已经包含在故事当中的悲剧。
而同时如果把整个电影拉开来,把好像折叠在一个魔盒里面的世界打开来的时候,里面其实是20世纪的历史,是20世纪这个极端年代里,各种故事的无穷回声。

(图片来源于看理想及网络,侵删。)
毕加索艺术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幕 展期至8月31日
“黑神话:悟空”主题艺术展|为情怀更为艺术
古人那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印章
故宫特展来了!172件文物感受希腊克里特岛的神话
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之美”)
越剧《红楼梦2025版》舞台版和电影项目启幕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守宝人丨云端守寺三十载
贵州:油菜花海绽春光
中转式旅游:追求“高性价比”与“松弛感”
蛇年寻“蛇”—— 藏在山西博物院里的“蛇”
“冰雪热”遇上“非遗热”,真燃!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理想的都城,秩序的杰作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相关新闻
2020要上映的好莱坞大片 这15部最值得期待
今年的好莱坞大片,虽然没有了像《复仇者联盟4》这样的巨无霸,但依然有像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信条》这样万众期待的类型片,也有根据中国故事改编而成的真人电影《花木兰》,依然精彩纷呈。
跟随《音乐之声》,探索千年古城萨尔茨堡
“群山活跃在音乐之声里,唱着已流传千年的歌曲;群山以音乐灌溉我心灵,我愿高唱每首听到的歌曲。” 在电影《音乐之声》开头,主角玛丽亚雀跃于阿尔卑斯山间,吟唱着这首动听的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