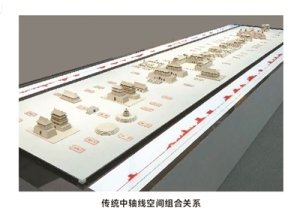曾用声音为我们打开世界窗口的超级巨星
本世界纯属非虚构

译制片曾是国人看世界的窗口,也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它迎来了黄金时期,配音演员也成了超级巨星,但译制片不再受瞩目后,他们也随之面临窘境:江湖地位犹在,却乏人问津。
缔造和走过黄金时代的人,会如何守候这个行业?
冷暖人生《出山》1
“年轻人”
“哦,我的老伙计”是我对译制片最直接而且深刻的印象:发音饱满标准,带有特别的韵律。这种腔调和演绎曾构成几代国人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一种基于观摩和想象被建构出来的银幕真实。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译制片是一种朦胧遥远的父辈记忆,充满了年代感和怀旧色彩。综艺节目总喜欢邀请配音演员,台前幕后的形象差距营造的戏剧效果总能让观众惊呼“神奇”。此前一款配音类的应用程序也颇受欢迎,某种程度来说,配音是年轻人的一种游戏。

《碟中谍3》截图
为什么这么高频次地提到“年轻人”?
所谓时代更迭,各行各业都面临危机,寻找出口。“年轻人”意味着未来的潮流,所有人都在揣度和瞄准这个群体的口味。
77岁的乔榛接到一档配音类综艺节目邀约的时候,心里有些别扭。他怀疑现场的年轻人到底认不认识他,是不是真的热爱译制艺术;更反感把配音当成游戏——作为从业五十多年的语言表演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创作就应该是严肃的”。

乔榛上综艺节目
这档节目已经播出两季,视频网站总播放量超过20亿次,主要观众群体是90后。
乔榛1970年开始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他是《叶塞尼亚》中的奥斯瓦尔多,《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西蒙,《生死恋》中的大宫熊二……八十年代是中国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上译厂是最重要的阵地,乔榛和群星们一起缔造了辉煌。

乔榛
然而九十年代以来,译制片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看着行业由盛转衰,乔榛一度非常绝望,“译制配音艺术是不是要死了”。2009年他突发脑梗,死里逃生,此后一切行动都需要依靠拐杖,但如今他依然活跃在各大舞台上,“不甘,绝对不甘”,他说。
“老年人”
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这是十年封闭之后第一部在中国上映的外国电影,日本媒体猜测至少8亿中国人观看了影片。女主角真由美在马背上对身后的杜丘说的一句“我喜欢你”,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大胆的告白。

《追捕》截图
听到这几个字不加修饰地表露时,刘钦脸红心跳,“是震撼”,他对我连续说了三遍,“这是带有羞耻感的东西,那时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刘风则觉得译制片里的对白“不像人的声音”,从小到大没听过身边有人这样说话,好听,洋气,遥远。
张欣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演译制片里的桥段。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他发现原来游击队不都是土布褂子白头巾的“老乡”扮相,还可以穿西装,戴帽子。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截图
他们生于六七十年代,译制片伴随了他们整个青春,除了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们人生的启蒙导师。
“虽然我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你同我,是拉着手一样拉着手,越过坟墓走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电影《简爱》的台词,上大学时,刘风和同学们都会背这一段。看这部电影之前,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精神的,哲学的,关乎自由平等与人性的,也关于爱情。

刘风
刘风,张欣和刘钦都是在译制片鼎盛时期入行的年轻人,配音生涯接近三十年。现在他们自称“老年人”——看着译制片长大的“老年人”,担心译制片也只活在老年人的回忆里。
黄金时代
上世纪80年代,乔榛去西安参加过一次颁奖,火车刚进站就有人追车喊他的名字,给他戴大红花;在武汉,热心观众围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说要克隆乔榛,最后真的用倒模“克隆”了他的手和嘴。

配音中的乔榛
改革开放后,译制片迎来了黄金时代,最多的一年引进的译制片在五十部以上,《尼罗河上的惨案》《魂断蓝桥》《叶塞尼亚》《茜茜公主》……带着大胆的情感和丰富的题材,就像是吹进中国的一派春风。影院门口总是大排长龙,有人为了抢个好位置甚至会大打出手。而除了一个个经典角色,他们的中文代言人,那些配音演员,也成了超级明星。孙道临,李梓,刘广宁,乔榛,童自荣…一个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尼罗河上的惨案》截图
刘广宁1939年出生于香港,四岁举家迁往上海。刘广宁的祖父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她从小就喜欢看家里堆满的各国名著,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少女。1960年,听说上译厂招收配音员,高中毕业的她毫不犹豫写了一封自荐信,自此开始了配音生涯。二十二年间,她参与了三百多部影片的配音,被称为配音殿堂永远的公主。

年轻时候的刘广宁
配音演员们经常收到来信,有人在信里请刘广宁介绍个配音演员“谈朋友”,她哭笑不得,“年轻人脑子单纯,以为配音演员和银幕上的演员是一样的,实际上给王宫侯爵配音的,是一群穿着打满补丁衬衫的男演员”。
业务很繁忙,加班加点是常见的事,即使不在工作,演员们也总在练台词。刘广宁经常吃着饭就突然“啊”地一声——那是她琢磨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回家之后,等孩子们写完作业睡觉了,她终于有机会就着台灯对台词,有一次忘情,“来一杯巧克力”说得有点过响,孩子们马上醒来冲她惊喜地问,“是给我的巧克力吗?”

刘广宁
上译厂是个金字招牌,和盛名不相符的是演员们的工资,作为资深配音演员的刘广宁,当时一个月工资43元,偶尔还要靠稿费改善生活。录音间倒是和工资保持一致,那时条件简陋,没有混响设备,录制回声效果还需要“出外景”,把收音杆儿夹在楼道里收声。一次录制火灾的戏,演员们在深夜高喊“着火了”,吓得整栋楼的居民都跑了出来,那之后,凡是夜间在外录音,都要提前和居民打好招呼。
不过,条件艰苦的上译厂依然是无数人魂牵梦绕的“艺术殿堂”。

上译厂合影
刘风1967年出生在吉林长春,父亲是舞蹈家,母亲是歌舞剧演员,他在文艺单位家属大院长大,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随后进入上译厂,还被同学们羡慕了一把,“这是个能出作品的地方,好单位”。
他给许多猫配过音,加菲猫,功夫熊猫……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只猫,他也是汤姆克鲁斯,尼古拉斯凯奇,裘德洛的“中文代言人”。

刘风
张欣的嗓音偏高偏尖,能驾驭语速快,难度大的角色,《尖峰时刻》里的黑人卡特是他在上译厂配的第一个角色,处女秀就获得了肯定。但他最喜欢配的角色不是超级英雄,而是小人物,上一个让他满意的作品是《海边的曼彻斯特》,配完之后久久无法出戏,张欣在配音间里呆了半天。

张欣
在译制片大行其道的年代,他们组成了配音演员的中坚力量,而为了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上译厂开始广泛吸收社会人才,从小就痴迷译制片的刘钦果断报名。
刘钦1963年出生在山东菏泽,从小热衷文艺表演,大学毕业后,学工科的刘钦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还和几个爱好配音的朋友一起租过录音棚,自己配电影玩儿。本以为和译制片的缘分仅止于此,这次终于抓住了机会。通过考核开始兼职后,刘钦每天下班后都要坐公交车辗转两三个小时到上译厂,经常加班到凌晨一点,再坐夜宵车回家,walkman里的一盘带子听完也就到家了,如此坚持了十年。

刘钦
上译厂配音一直遵循一套完整的“工艺”:翻译,调整,对戏磨合,录制,鉴定补戏,一部片子完成译制往往需要一个月。刘风记得自己有一次要配一段笑声,笑了二三十遍嗓子都哑了依然不到位,最后是音色相近的乔榛“帮他笑”——这让他受宠若惊。
过去配音不分轨道,画面上有多少演员,录音棚里就有多少配音员,新老演员挤在一起,最多时挤了十多个人,因为靠得太近,演员们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配音前不能吃大蒜。
上译厂的出品质量也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乔榛回忆,好几批国际影坛的权威人士来参观后都拍案叫绝,“你们是全世界译制艺术NO.1。”
冷暖人生《出山》3
“四人帮看的黄片”
然而黄金时代到来之前,译制片曾是少数人的“特权”。
乔榛1942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热衷于朗诵,演话剧,有同学为了表达仰慕,还会“跟踪”他一起放学回家。带着建设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革命理想,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但艺术生涯刚开始就遭遇了变故。

年轻时候的乔榛
1966年之后的十年,绝大部分文艺工作停止,国人的精神娱乐只能寄托于样板戏。那时乔榛刚从大学毕业,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演员。对满腔抱负的乔榛来说,未来一片迷茫。文艺单位是“牛鬼蛇神”的重灾区,昔日的电影明星被一个个打倒在地,他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偶尔在河边练台词段子,还会被工宣队批评“走白专道路”。
转机发生在1970年。乔榛接到任务,去上海电影译制厂参加一次配音,“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大哭一场,总算又能从事艺术创造了。”

年轻时候的乔榛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下来的政治任务”:为高层配译参考片,也就是内参片。从诞生之初,内参片就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常有人传言内参片是四人帮看的“黄片”,外国电影都是“毒草”,“宣扬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鼓吹阶级调和……”,从配音间里出来,演员们还要开大会自我批斗,“肃清流毒”,“其实我们都彼此笑话,心里都有数,但是不敢说什么。社会风气是那样,不敢行差踏错”。
有一次,刘广宁把剧本弄丢了,吓得肚子疼了半天,后来才知道是图书管理员收了回去,立刻松了一口气。任务紧张,配音演员加班加点经常在厂里打地铺,刘广宁曾顶着高烧配音,完成之后几乎失声。

刘广宁在配音
不过还能从事创作的“幸存者”们已经感到非常幸运,配音间俨然成了一个乌托邦。全国上下闹革命的同时,国外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守着这个窗口看得目瞪口呆,对外依然只能三缄其口。
十岁时,刘风跟着父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看过一部参考片,《安娜卡列尼娜》,三百人影院被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不少人蹲在一边,院子里也挤满了人,很多是偷偷翻墙进来的。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安娜卡列尼娜》截图
印象中电影很长,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刘风看不懂,也听不懂,他看得直犯困,回头一看,所有的大人都全神贯注,“眼睛紧紧盯着屏幕,都不说话,如饥似渴的。”
式微
正因为内参片配译的需要,上译厂很快集结起第一代演员,并钻研出一套“工艺流程”,逐渐成为译制片制作最重要的阵地。1978年后,一批内参片“重见天日”,立刻掀起一阵风潮,“《出水芙蓉》,过去那都是美国人的大腿片”,“荒漠了那么长的时间,终于有这样一股风刮进来,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大家的心里会多么激动。”

为影片配音的演员们
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新的娱乐形式出现,影院改成舞厅歌厅,电影变成录像带传到街边音像店,译制片也不再是看世界的唯一渠道,观众越来越少。
“那个时候都在看谁能赚钱,没人看这个了”,作为在鼎盛时期入行的从业者,对行业和自己的未来,刘风突然陷入了迷茫和纠结。配音的活儿少了,困境中,一些演员离开了录音棚,下海经商或者出国留学。他自己也尝试了其他行业,拍广告,做外贸,还开了饭馆,东北饭馆生意不错,比在厂里挣得多得多。刘钦和张欣给一些网络游戏配音,甚至被当成了他们的代表作。
外患伴随着内忧,创业之初的一批艺术家也陆续到了退休的年纪,刘钦还记得,《虎口脱险》《冷酷的心》等影片的配音演员尚华,颤颤巍巍口齿不灵,最后是哭着离开了话筒,“倾注了一辈子心血,干不了当然是一种打击”。

工作中的刘钦
10年前,借着动画电影的势头,译制片迎来了一次春天,演员们不论是“公主王子”专业户,还是影帝影后的御用代言人,都参与了动画片配音。然而这次春天很快过去。影视明星纷纷进场成为配音电影主角,国产片迅速崛起,引进的国外大片越来越多,这些重视听效果的影片,原声电影的吸引力远超过配音版本。

参与配音的影视明星
而另一方面,因为技术革新和工业化生产的需求,配音演员们开始独立录制成轨,少了磨合对戏等流程,比起巅峰时期,译制片本身的质量不可避免地下滑。“这个其实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我听他们说,轨道多了层次感就可以出来。如果不这样能不能也做到层次感呢?我不懂,我不能乱说”,乔榛还心心念念着过去一群人挤在一起配音的氛围。
出山
2005年,刘风的东北饭馆正办得红火,上海电影译制厂有了人事变动,他是副厂长的人选之一。那时译制片已经是“过时”的东西,逐渐退到了院线边缘,更多时候,它作为时代的记忆被提起。

上译厂旧址
行业的兴替不只发生在译制片领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在时代流转中不停上演,有多少正当红的事物在引领风潮,就有多少正在期待东山再起,而经历过甚至亲手缔造了黄金时代的人们,带着骄傲,不甘和遗憾,在困境和迷茫中尝试挣扎,结果还无从而知。
一番思考后,刘风关掉了餐厅。

录音中的刘风
2018年末,一个互联网音频平台向刘风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录制《红楼梦》的有声书。在这个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有声书,点播量接近40亿次。
一部《红楼梦》几百个角色,找谁配音?刘风首先想到了上译厂的群星。

上译厂演员配音
当刘风一一找到当年的巨星时,他们欣然献声,敬业地准备台本,讨论书中生僻词汇的发音。乔榛被邀请为贾政配音,张欣和刘钦同样是这部有声书的配音者,导演和制作人。《茜茜公主》中苏菲皇太后的配音者曹雷已经80岁,还多次辗转来到位于城市北边的录音棚。
他们要一起把握住这次互联网的机会。

《红楼梦》录制中
退休后,刘广宁去了香港教普通话,晚年回到上海定居。不久前,有个华裔诗人请她为自己的诗录制音频,诗人告诉她,很多人留言,说再次听到刘广宁的声音,唤醒了他们的记忆。过去他们听着配音演员的声音想象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活。

刘广宁
时至今日提到译制片,刘钦还能想起他小时候听《追捕》的录音剪辑。东京街头人潮涌动,马群奔跑,一句句台词吸引他继续往下听,听入迷了,他在家门口呆站了二十分钟。没有画面,只有收音机里传出的普通话对白,“对我来说它很神圣,所以我要捍卫它”,他说。


制片人:裴天懿
文&视频编导:郑逸桐
“黑神话:悟空”主题艺术展|为情怀更为艺术
古人那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印章
故宫特展来了!172件文物感受希腊克里特岛的神话
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之美”)
越剧《红楼梦2025版》舞台版和电影项目启幕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守宝人丨云端守寺三十载
贵州:油菜花海绽春光
中转式旅游:追求“高性价比”与“松弛感”
蛇年寻“蛇”—— 藏在山西博物院里的“蛇”
“冰雪热”遇上“非遗热”,真燃!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理想的都城,秩序的杰作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相关新闻
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这部纪录片聚焦中美企业文化差距
由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史蒂芬·伯格纳、茱莉亚·莱哈特执导,奈飞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在网上播放后,很快引起热议,成为一部现象级纪录片。
首创官方衍生品 上海国际电影节文创设计的吸睛之路
今年3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对外发布了本届电影节的海报,这幅由上影节委约海报设计师黄海创作的“创生万象,幕后为王”主题海报,主视觉灵感来源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大闹天宫》
《我和我的祖国》定档国庆 七大导演齐聚一部电影!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发布一组时尚大片与导演影像,影片的总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携手亮相,集结几代中国电影人力量,定格中国导演风采与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