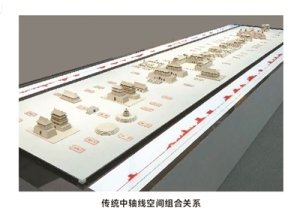邵光亭:书法艺术的现代性问题
(文/邵光亭)
书法艺术的现代性问题是个伪命题。作为华夏文化精粹的集中体现,中国书法最根本的特性是传统性,书写者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书法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书写者精神内涵自然流露的过程。一笔一划,字里行间,将书写者全部的品学修养淋淋尽致的展现出来,或雅或俗,一目了然。“书如其人”,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书法来不得半点虚假。书法艺术的群众基础是最广泛的,只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都能或深或浅的欣赏书法艺术之美。
书法不是行为艺术,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庄子》中有一篇寓言,宋元君命人作画,画师一个个濡笔调墨,看上去阵仗很大。有一人后到,舒闲从容,行礼已毕即返回自己的住所。宋元君派人去看,只见他解衣盘礴,撩起袖子信笔挥洒。宋元君感慨说“这才是真正的大画师”。故事中宋元君的话,描述了一个“真画者”的状态。书画同源,其理一也。成为一名书法家并非易事,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积累与沉淀,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在笔者看来,那些故弄玄虚以各种所谓“特技”进行“书法表演”的人,“多数都是没有书法功底或者天赋不高,难以通过正当途径被大家认可又急于出名的人”。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博众人眼球,都是市井江湖的伎俩。书法艺术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富矿,自然可以为其他艺术形式提供借鉴,也可以衍生出新的艺术形式。但作为艺术本身,是神圣的、高尚的。经典变成了恶搞,不仅是艺术的悲哀,也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作为文化工作者,有责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展示中国文化的自信。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提出“文化书法”这个概念,我并不完全认同。书法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书法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将文化思想资源注入书法艺术领域,书法本身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呈现的一种方式。古人说“书者,小道”,写一手好字是读书人的必备基本技能,“善书”是大学问家的风雅所及。当代书法创作的问题,不在于文化超越性,而是创作者文化根基不深。书法是一种文化思考和精神探索,必须始终坚持中国书法的根本品格。目击道存,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书法是中国文化的审美呈现,书法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不是唯技术主义的程式化制作。
书法的内涵体现的是文化品味和人文追求,创作者的文化、思想浓缩在笔墨线条之中。发掘书法之美,要回归传统、回归经典。形质格调简净淡远,笔墨意趣萧疏儒雅,是书法的审美准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规定性的要求。只有具备较高的学识修养,笔底才能有意蕴。饶宗颐先生说:“书法就是文化,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讨论。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学问,是有很高的文化含量的”。书法艺术的不朽魅力和独特性格在于,通过简单的线条、形态、笔墨、留白等的抽象造型,表现出力、势、骨、气、趣的深层美感和丰富内涵。
心灵的感触与现实世界的体会往往形成对立的矛盾,矛盾的激化造成人社会生活的紧张状态。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书法艺术的形式、气韵、境界,渗透于人的心灵深处。人格修为,哲学之思与书法相互贯通,线条形态的长短、曲直、大小、方圆、正斜、燥润、轻重、刚柔、粗细、强弱、抑扬、进退、疾徐、动静、聚散、疏密、虚实、离合、巧拙等,深刻反映主体性的灵魂律动。李泽厚所说的书法艺术审美的体验性“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层次,正是传统文化强调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和谐统一的精神所在。书法的内容、境界,蕴藏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审美观念。唐代孙过庭云:“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既是形式的和谐,又直指人的心灵世界。具有恒久的魅力,不因时空的变幻而改易。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一些人以书法的现代性为名,大兴“丑书”之风,只看今朝,不顾来日;无视传统,与社会主流观念和意识背道而行。所谓的创新与变通,不过是在皮毛和外形,与书法的艺术精神相去甚远。
我曾公开表示,要旗帜鲜明的反对丑书。有人说“丑得精彩而不能欣赏”,那是大众的审美太幼稚了。“中国古代对所有的风格都很包容,并不论美丑,只论格调”。这是什么逻辑?这种观点有什么历史依据?几千年来,书法艺术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多少人为之痴迷,为之倾倒,穷尽毕生心血,追求艺术的至善至美。当今书坛极尽狂怪的丑书,完全背离了书法艺术规律。有些所谓的书法家,胸无点墨,实则是文化骗子,贻笑大方,更贻害大方。
有人以言论自由、文化包容为由为丑书遮羞辩解,制造出很多奇谈怪论,诸如“愈丑愈美”说、“书写性情”说等等。加上一些人的推波助澜,让丑书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学术讨论固然不能打棍子、扣帽子,对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应该理解包容。但是这绝不表示没有是非,放弃立场。《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没有原则,看似忠厚实际只知道媚俗趋时的人,不但混淆视听,也严重伤害了学术生态。对此,我们要态度鲜明的予以回应。
很多人以傅山的“四宁四勿”来论证丑书的合理性,实际上傅山所说的“宁”和“勿”,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在丑和媚之间,宁可偏丑。媚的含义古今有别,并不是单纯的指有魅力。媚,从女,眉声,表示以目示人,有逢迎之意。《史记•佞幸传》:“非独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在古人看来,媚比丑更可恶。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媚固然不足取,但也不表示丑就有价值。当代书法的大问题在于但求轰动效果,不但丑,很多甚至“丑”得没有道理。格调低俗,背离了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律,扭捏状态,令人作呕。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首先要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果人们连看都不愿多看,望而生厌,这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歪歪斜斜,既丑且怪,表面繁荣的背后,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是钻文化的空子。
对于当代书法而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现代性的转换,而是全面、彻底的回归传统,匡正名实,以全面、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提升创作的思想内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书法是厚重的中国文化的代表,无论时事怎样变幻,书法研究者都应保持定力,书法创作者当以深厚的学养、功力和开阔的胸怀,实现超越与突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砥砺品学,固本强基,书法才有未来。
传统文人有两种特质:一是学识胸怀,二是风骨情操。既不崇敬学问,也不敬畏古人,顽固傲气,从心所欲,不知自警自惕。我看到一些鼓吹现代书法的先生后生们,连书法创作最基础的文字关都不及格,下笔错漏百出,谬种流传。不仅无临帖之功,刻意求怪,自诩为艺术,冠之以“现代派”,说白了就是盲求捷径。没有高深的文化造诣,不可能成为名冠古今的大家。名为现代派,实为“江湖体”“野狐禅”,不要说窥得宫室之美,根本就是没入门,更不要说入流了。当下书法界呵祖骂佛,离经叛道者比比皆是。“风骨”缺失,“情操”扫地,值得反思。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不薄今人爱古人”。艺术创作,在守成中有突破,在突破中蕴传承。单纯凭技术的高低很难深人中国书法的内核,不能使书法走向美术化、工艺化的穷途末路。
道听途说,德之弃也。有人说元代杨维桢的书法也是“丑书”。这种“丑”实际上是一种古雅之美,与当代丑书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杨维桢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为人旷达,有晋人遗风。杨维桢书法的价值,有特定时代的因素。有元一代的书法创作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很多人甚至放弃追古,而直接学习赵孟頫,时弊积重难返。元代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很多文人选择归隐避世。杨维桢书法的粗头乱服,点画狼藉,不计工拙,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反映,是内心苦闷情绪和困乱时局的折射,并非刻意的求新求变。乍看之下给人一种偏离正统的怪异之感,“细细品味之后则感觉狂而不乱,虽纵横交错却浑然一体”。杨维桢的这种“丑书”,在当时的书坛反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入古”基础上的“出新”,师承古法,毫无熟媚绰约的“贱态”(傅山语)。
杨维桢的书法,尚属正脉。取法魏晋,盖自《兰亭》稍变而至此,又融入欧阳询的险绝风格,用笔方整厚重,骨力洞达。行笔多以中锋,结字之舒密多继承传统,非主观臆造。章法萦带生动,结字体势恢弘,线条如棉裹铁,性情高逸,自然天成。充满高古奇崛之趣,是当时书坛的一股清流。
南北朝虞龢的《论书表》云:“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书法以“质”为上,应以古为师。知本末,好行藏,彬彬文质,有根有源。对于书法创作来说,技巧是基础,不是全部。妍美只是一种表象,不能长久。技术的精益求精是重要内容,不是主要内容。书法的文化意义,在于教会我们敬畏经典、崇尚经典。艺术有一般性的规律,神乎其技,技进乎道。当代书法,或者说现代性书法的唯技术化倾向,并不是正确的方向。把书法拉低、停留在形而下之的境界。任何只重形式的低级趣味,都不可能行之久远。
启功先生曾说“学业之余,则以学书,胜博奕饮酒,得身心之娱”。一直以来,书法都是文人雅士业余修养身心的“小道”。但小道也是“道”,有成法、有规矩、有标准。商承祚先生有言曰:“书法遵大道,思绪莫歧途。”八法薪火相传,砚田耕耘挥毫篆籀,须追摹前哲,方能驾锺王而让后贤。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的艺术观念,流行新的艺术思潮,形成时代风貌。御今执古,承旧开新,书法作为一门民族的、独特的传统艺术,当然要发展。但是应该明确,“新的”未必一定是“好的”;鼓励创新,也不表示不能对创新的成果进行批判。文化多元,也不是书法审美格调低俗的理由。尊重艺术创造的独立性,尊重艺术家的个性,保障各种艺术探索的基本权利,固然没错,但要守住底线,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品格。必须坚持和尊重艺术规律。审美观与形式风格的多样性,不是评断书法作品艺术水平的依据,个性与美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人认为,批判现代书法、指斥丑书,是不懂美学。按照辩证法原理,美与丑总是相对的,艺术审美中的美与丑也是可以转化的。但不是说美即是丑,丑也是美。常识是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来辩解,也不能混淆美与丑的边界。艺术家的天职是发现美,拓展传统的审美界域,以优秀的艺术作品提高大众对审美从广度到深度的认知水平。因此,重重迷雾之中,就有廓清的必要。如果美丑不辨,就没有深入讨论的基础,对书法艺术和民族文化复兴也是极大的伤害。
我一再强调,书法不是单纯的视觉艺术,她有着浓重的文化属性。现代书法、流行书风、丑书等,其根本问题不是把字写得歪斜变形,怪诞夸张。把字写得端正整齐,也不是评价书法艺术高低的终极标准。中国书法史上,一种书体的出现,一个时代书风的形成,一个书家风格的确立,不唯形变而已,不是靠简单的形态变化。书法审美,是形、气、韵、神、境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可视、可感,还要可品、可思、可悟。传统不是枷锁,不同时代在审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本不足为奇。我之所以反对现代书法,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弊端。当代“主流”的书法创作,所谓的张扬个性和主体意识,为创新而创新,以粗疏代替丰富,以肤浅置换深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重形式轻内涵,装饰意识的引入,注重视觉效应和求新求异,逐渐消弭着书法艺术的固有精神,使当代书法创作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
宋代蔡襄曰:“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书法审美贴近现实,贴近大众,其美丑、优劣是很难造假的,包装消费可以行得一时,但绝不可长久。现代书法的探索,希望打破书法的传统艺术样式,在现代抽象图式上寻求可能,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将装饰风潮奉为圭臬的趋势。有人说:“人们不懂的,才是艺术,才是美。”这种论调需要警惕。脱离传统的现代书法,或挟洋自重,或以现代思潮、现代审美自许,舍本逐末,少真而多恶俗,全无笔法,又谈何书法?“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这是很高的要求。对于书法来说,神采附丽于笔墨,笔墨情致,是需要长期的学习领悟出来的。书法可以有创新,但没有现代派。丑书或者现代书法作品让人看不懂,很多所谓“书法家”“书法大师”,其实是“正道难进”而走“歪门邪道”以“谋求名利”。一直以来就没有被正名过的所谓“现代派”,“中国从来就没有过靠花样成功的大师”(陈传席语)。“现代派”书法只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是一个伪命题,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拉大旗作虎皮”的手段。
思想浮躁了,社会整体都会浮躁起来。“现代派”书法看似繁荣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虚无与堕落!不仅与传统背道而驰,造作媚俗,笔触突兀,外无金玉,败絮其内,传达的是压抑、扭曲、畸变的窘困惶惑,鲜有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深度与情思。
书法的技巧很平易,不要用概念忽悠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艺术创作,都要不失风骨,有一点志气,努力摆脱流行的绮靡之风。书法流于技术化、装置化、形式化、表面化甚至文盲化,至为可悲。有人说丑书也是美,丑书从美学的角度看是美的,这是狡辩之词、强盗逻辑。美学归根到底还是要以美为最终的判定标准,离开了这个标准,就是谬论。美丑与否不是靠一些故弄玄虚的概念包装出来的,丑书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丑的。漫漫历史长河,任凭百家争鸣,大众与历史是评判书法美丑的唯一标准,大浪淘沙,所有愚弄大众时代行为终将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书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传统文化是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背景。现代书法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本质属性,使书法走向极端化道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书法艺术的张力,不在于现代派所鼓吹的夸张形体。中国古典人文理想、人文精神,造就了一代代无愧于时代的精英。在新的历史时期,书法作为古典人文理想的代表,为净化和修复现代大工业化时代人的焦虑,对建立民族精神家园,为人类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提供了广阔空间。正道沧桑,必须正本清源,对那些俗不可耐、旁门左道的所谓书法艺术,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匤正书法艺术的审美情趣。
(作者简介:邵光亭,经学史学者,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其书法精妙,诸体兼擅;绘画攻山水,笔墨酣畅,清新俊逸。于诗、书、画、印等方面皆有深厚造诣,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多有建树。)
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之美”)
越剧《红楼梦2025版》舞台版和电影项目启幕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守宝人丨云端守寺三十载
贵州:油菜花海绽春光
中转式旅游:追求“高性价比”与“松弛感”
蛇年寻“蛇”—— 藏在山西博物院里的“蛇”
“冰雪热”遇上“非遗热”,真燃!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理想的都城,秩序的杰作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相关新闻
当代书法家:孔可立作品欣赏
从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后虚怀若谷,,孔可立追求作品的美感和思想纯度,不断挑战书法创作的固有模式,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辛求索之路。其作品旷达飘逸、苍利隽秀、时出天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