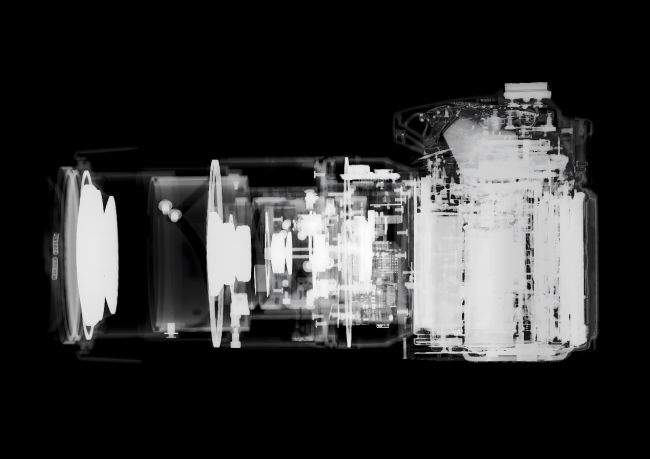为什么仰韶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仰韶文化花瓣纹彩陶盆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大会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贺信肯定了100年来几代考古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对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希冀。这封贺信不但鼓舞、振奋了考古界,也使得这场会议获得全国高度关注,仰韶遗址也被再次聚焦。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地方。100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了仰韶遗址,这成为考古界公认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安特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绕不开的人物。其实,自清末以来,除安特生之外,也有不少外国学者和探险家在中国进行考察和探险活动,比较著名的有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科兹洛夫、鸟居龙藏等。但是,为何是安特生而不是其他人,以及是他在仰韶村的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我们就这个问题略作讨论。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本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1914年,他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协助中国人寻找煤矿和铁矿。后来,由于时局的动荡,找矿工作难以开展,他遂转向古生物化石的收集。由于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过程中往往能采集到石器,他的兴趣继而又转向了考古。1921年1月,安特生通过助手刘长山从河南仰韶村采集回来的磨制石器推断,仰韶村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年4月,安特生亲赴仰韶村调查,在冲沟断面上发现彩陶与石器共存的现象,从而断定仰韶村是一处遗存丰富的史前遗址,值得发掘。于是,自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主持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共发掘17个遗址点、 10座墓葬,发现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文化层平均厚度达3米,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1923年,安特生以仰韶遗址发掘所得的材料为基础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汉族人遗存,时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者稍晚。该书的发表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在当时直至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力。
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其贡献不仅仅是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史前文化,而且在于他引入了科学的理念,创立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使考古工作从此变得科学和规范,并为后来的考古工作者所效法、沿用。如果对比他之前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的活动,则更能显出其重大价值。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在发掘方法上,安特生率先使用了“探沟法”进行发掘。所谓探沟,是在遗址内划定一定规格的矩形区域,考古发掘就在此区域内进行。由于探沟形状方正,有利于出土器物坐标的测量和记录;另外,沟壁上有剖面可供观察,有利于把握地层;同时,可以用较少的时力,便可弄明遗址内的地层堆积情况。这种发掘方法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实属首次。安特生之前的外国学者和探险家,在中国境内的探险和考察活动,基本以调查为主,偶尔会有发掘,但没有使用探沟法进行发掘者,而且有的发掘方法实在难称高明。比如,德国人范莱考克在新疆地区使用的粗糙的发掘方法甚至让斯坦因感觉到厌恶。后来,探沟法被中国考古界一直沿用,并演进出“探方法”。
2、安特生引入了新的发掘工具。手铲和毛刷就是此时被引入的。安特生从实践中认识到,在剔人骨和易碎陶器时,这两样工具尤为得力。这些工具在考古界沿用至今。特别是手铲,现已经成为考古工作者的标志性工具,甚至考古界设有“金手铲奖”。
3、对于出土器物,安特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重要遗物,会用三维坐标法进行测量;陶片和石器等一般遗物,则按照发掘深度,详细记录数量、种类和特性,并根据质料和颜色进行分类。这种记录方法,已与现在田野考古的记录方法很接近。这无疑为后来发掘资料的整理和使用提供了便利。正如著名学者胡适在日记中所记录:“他(指安特生)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如果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察,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比如1909年6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掘开了黑水城内西城墙的一处佛塔(这被科氏称为“辉煌舍利塔”),发现了大量的书籍、簿册、经卷和佛画。他用了9天的时间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搬空。但是这批文献情形十分混乱,而且当时科兹洛夫又没有留下任何发掘记录,以至于后之学者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对其进行整理。
4、安特生十分重视遗址的地形测量及调查。由于安特生是地质学家,他对地形地貌非常关心。他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绘制地形图。在仰韶遗址,他让袁复礼绘制了仰韶遗址的地形图(1:4000),他本人则绘制仰韶遗址南部的等高线图和地形剖面图(1:2000)。而这些图在以后的研究中很有参考价值。另外,安特生认为了解地形地貌是研究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毕竟年代越早,人类受制于自然因素越大,所以考察这些对于了解史前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非常有益。
5、安特生采用了多学科合作的方法。仰韶遗址当时的发掘成员,除了安特生本人外,还有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地质学家袁复礼、人类学家步达生。发掘完毕后所得人骨材料由步达生研究,动物骨骼由瑞典的达尔博士研究,陶器的化学成分,安特生也邀请专人进行检测。值得注意的是,在仰韶遗址的一件陶器上,有植物种子印痕。安特生请瑞典植物学家爱德曼和索德伯格进行研究,后来鉴定这是一种水稻壳。此后,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文章中无不提到安特生的这一发现。多学科合作,自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传统,现在依然如此。

仰韶文化彩陶钵
除开这些技术层面上的做法,安特生的一些做法在当时中国也很超前,特别是跟同时代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相比。
1、在仰韶遗址正式发掘之前,安特生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进行了申请,他在得到批准之后才进行的考古发掘。而他之前的外国学者和探险家们在中国境内进行探险和考察活动,基本不会征询中国政府的意见。
2、在对出土文物的处置上,中瑞两国有过协议,中国和瑞典会将安特生在中国获得的文物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国。后来,安特生主持将文物分为7次退还给了中国。在现在看来,这种方式仍然不平等,但跟安特生之前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相比,实属难得的进步。比如,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人想方设法骗取敦煌藏经洞的文献运回本国,使得敦煌文献大量外流,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内将西夏文献抢掠殆尽,运至俄国,并秘而不宣,使得我国西夏学研究因文献资料匮乏而长期沉寂。所以,相比于这些强盗式的抢掠,安特生的做法显然更容易被接受。
3、在仰韶遗址发掘结束之后,安特生还特意在地堰上立牌,书“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这种文物保护意识实属难得。而其他外国学者和探险家与之相比,实在是相差天渊。比如,俄国人克莱门茨在吐鲁番考察,将古代庙宇上的壁画切割下来运往欧洲,开切割壁画之恶例;科兹洛夫为攫取黑水城内佛塔中的文献,几乎见塔就挖,这使得城内80%的佛塔都毁于一旦。
在当时的中国,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前后的这些做法,彰显了其正直善良的品格,以及作为一个优秀学者的良知,无疑更能获得国人的尊重,而且对中国考古学显然有更多正面影响,是一个良好开端。
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所言,这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另一种构建史前史的可能,中国学术界接纳之,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尽管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也有很多不足,但是其贡献是主要的。他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中国考古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如果考虑到安特生在发掘仰韶遗址时并非专业的考古学家,他能做到这些更属难得。而在他之前的探险家和学者,尽管在中国有诸多发现,但在方法上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与安特生的巨大贡献相比无法同日而语。所以,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遗址的发掘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中国考古人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之路,也从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开始。
作者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图片均来自河南省博物院官网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相关新闻
大仰韶:一个世纪的考古探索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
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出土青铜神树
日前,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掘区域的3号坑再次出土青铜神树。据3号坑发掘负责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介绍,今年3月份,这件青铜神树残件就在3号坑比较靠中心的位置露出了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