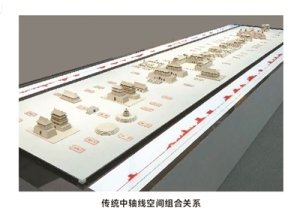读 7 位作家获奖演说 了解他们为何能得诺奖
诺奖每年一度的“开奖周”还在继续,10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出,将此次开奖周推向了高潮。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由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摘得。古尔纳是谁?为什么是他?点击领取答案。
依照惯例,每年12月10日,也就是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会举办诺奖颁奖典礼,当年各奖项获奖者受邀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仪式和晚宴,并参加获奖者讲座、音乐会等一系列“诺贝尔周”活动。受疫情影响,今年“诺贝尔周”延续去年的做法,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并且取消颁奖晚宴。
其实,“诺贝尔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奖演说,这应该是他们创作中最精华的一章。下文选取福克纳、马尔克斯、海明威、莫言等 7 位往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奖演讲,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除了都坦诚表达了相似的惶恐和感谢,这些作家也将写作视为自己一生的任务、视为探索未知领域的起点、视为介入社会的方式……
他们把写作作为自己工作或者职业的专业素养、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思索与关切,无论什么时候阅读,都具有十足的现实意义。
威廉·福克纳: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

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他因为“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194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的,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的。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要做出与这份奖赏原本的目的和意义相符,又与其奖金等价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话并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本身就能写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必须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做不到这样,将是白费气力。写出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情欲,写出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写出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糟的是没有怜悯或同情的胜利。写出的悲伤不是为了世上生灵,所以留下不深刻的痕迹。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重新懂得这些之前,写作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类能延续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的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延续,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
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们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获胜的支柱和栋梁。
海明威:我讲得已经太多了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1954年,海明威以他的小说《老人与海》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健康不佳,患有多种疾病且精神抑郁”,海明威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撰写了一篇演讲辞。不过这时他恰好在古巴,迷恋钓鱼、打猎,经常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桑提亚哥一样照常驾艇出海去钓鱼。
我不善辞令,缺乏演说的才能,只想感谢阿弗雷德.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们慷慨授予我这项奖金。
没有一个作家,当他知道在他以前不少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此项奖金的时候,能够心安理得领奖而不感到受之有愧。这里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作家的名字。在坐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学识和良心提出自己的名单来。要求我国的大使在这儿宣读一篇演说,把一个作家心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说尽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人理解,在这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十分清晰起来,根据它们以及作家所具有的点石成金本领的大小,他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作家的组织固然可以排遣他们的孤独,但是我怀疑它们未必能够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孤独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 这样他就有幸会获得成功。
如果已经写好的作品,仅仅换一种方法又可以重新写出来那么文学创作就显得太轻而易举了。我们的前辈大师们留下了伟大的业绩,正因为如此,一个普通作家常常被他们逼人的光辉驱赶到远离他可能到达的地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作为一个作家,我讲得已经太多了。作家应当把自己要说的话写下来,而不是讲出来,再一次谢谢大家了。
加缪:我们要防止这世界分崩离析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因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授奖词补充道: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地问题,这种热切的愿望无疑地符合诺贝尔奖为之而设立地理想主义目标。同年,加缪发表了获奖致辞《写作的光荣》,下文为节选。
秉承自由精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份殊荣授予我,万分感激之余更添万般惶愧……面对命运的过度垂青,想要重归平静,唯有力求问心无愧。既然我所做的一切与此盛誉颇不相称,别无他法,只有拿一生中最险恶的逆境下支撑我的信念来应对:对艺术的信念,对作家这一角色的信念。
作家的角色责任重大。 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的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这两个信仰足以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
如果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数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茫然无助,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的历史是腐化的,混杂着失败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疲弱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之中,政权能摧毁今天的一切,却并不能说服,智者自贬身价成为了仇视和压迫的奴役。
这代人不得不带着独有的清醒,为自身和周围修复一点点生存和死亡的尊严。在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世界面前,审查官建立的恐怕是永久死亡的国度。这代人明白,在与时间疯狂赛跑的同时,他们应在不同民族间建立不屈于任何强权的和平,调和劳动与文化的关系,在每个人心里重建和解的桥梁。
能否完成这一使命还是未知数,但在世界各处,他们祭起真理和自由的大旗,必要时,愿意为此牺牲而无怨无悔。这一代人在哪里都值得敬重、值得鼓励,尤其是在他们献身的地方。总之,应该是向他们,献上你们刚刚赋予我的荣耀,我想你们也会深有同感。
马尔克斯: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文学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82年,马尔克斯获玛贝尔文学奖,因其“在长篇小说代表作《百年孤独》中,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幻象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命与斗争。”同年,马尔克斯发表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获奖演说,下文为节选。
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
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
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 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布罗茨基:首先在于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美籍俄罗斯诗人,代表作有《诗选》(1973)、散文集《小于一》(1986)、《论悲伤与理智》(1996)等;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被授予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下文获奖演讲有节选。
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独特的面部表情”。在这一独特表情的获得中,也许就包含有个性存在的意思,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已有了似乎是遗传的准备。
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在于:他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是最高尚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
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上,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需要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其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可敬名称的命运。
一般的艺术,其中包括文学,愈是出色,它和总是充满重复的生活的区别就愈大。在日常生活中,您可以把同样一个笑话说上三遍,再说三遍,引起笑声,从而成为交际场合的主角。在艺术中,这一行为方式却被称为“复制”。
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孔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形为文学的(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就已自然而然地,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也会成为免遭奴役的一种保护方式。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就较少受到重复的各种政治煽动形式和节律咒语的感染。
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创作出杰出的保证,而且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 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那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
辛波斯卡:灵感总会造访
那些自觉选择职业并爱工作的人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2012年2月1日),波兰诗人、翻译家。辛波斯卡一生创作了二十本诗集,公开发表诗歌约400首,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延续至2012年,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巨大的数目》在1976年出版时,首印1万册在1周内就售罄。因其诗作“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于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下文获奖演讲有节选。
据说任何演说的第一句话一向是最困难的,现在这对我已不成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行——对我都是一样的困难。
被问及何谓灵感或是否真有灵感之时,当代诗人会含糊其辞。这并非他们未曾感受过此一内在激力之喜悦,而是你很难向别人解说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几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也躲闪规避。不过我的答复是:大体而言,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属特权;现在,过去和以后,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那些自觉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象力去经营工作的人。这或许包括医生,老师,园丁——还可以列举出上百项行业。只要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他们的工作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困难和挫败绝对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不论灵感是什么,它衍生自接连不断的“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并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们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他人而受到重视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对人类是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而就目前情势看来,未来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因此,虽然我不认为灵感是诗人的专利,但我将他们归类为受幸运之神眷顾的精英团体。
尽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许存有某些疑惑。各类的拷问者,专制者,狂热分子,以一些大声疾呼的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也喜爱他们工作,也以富创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们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为那或许会减弱他们的主张的说服力。任何知识若无法引发新的疑问,便会快速灭绝:它无法维持赖以存活所需之温度。以古今历史为借镜,此一情况发展至极端时,会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这短短数字的原因了。这词汇虽小,却张着强有力的翅膀飞翔。它扩大我们的生活领域,使之涵盖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如果牛顿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园地面上的那些苹果或许只像冰雹一般;他顶多弯下身子捡取,然后大快朵颐一番。
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摒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
莫言: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

莫言(1955年2月17日-),中国当代作家,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其“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颁奖典礼上,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宣读颁奖词:“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其后,莫言身着胸前刺绣着“莫言”两字红色篆刻图案的深色中山装,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下文为节选。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