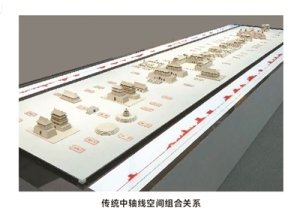汉代神兽︱镇墓的天禄、辟邪如何演变成宅门前的石狮子?(3)

洛阳孙旗屯出土一对有翼石兽(上图版承霍宏伟先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展厅拍摄;下图版采自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黄河文明展》,中日新闻社,1986年,第122页)
这对石兽的整体造型都呈“S”形,行走状,质地为青灰色石灰岩,独角兽全身被淡红色土锈所包裹。独角兽首略向右偏,双角兽首则是微向左偏。面部五官清晰,双目圆睁,眼部线条狭长而流畅,内眦开角宽阔,好框入其中又大又圆的瞳孔,而上边一抹眼线自前往后勾勒出先扬后抑的线条、到眼角处又斜飞延伸,呈现出近似丹凤眼的眼型,格外神采奕奕。眼角之后,各自两只椭圆形的耳朵挨着头部向后斜伸。两兽的鼻子顺着面庞上仰,露出两只鼻孔。鼻子下,各自的大嘴张开,各露出上下的一排牙齿,下排可见獠牙,舌头均向上翘起,似乎它们正在咆哮,引来雷霆万钧。下颌各一条长须垂胸。
两兽颈部略微前伸,颈项上部皆阴刻七字隶书铭文“缑氏蒿聚成奴作”。它们的身形矫健,前胸挺起,呈现出昂首挺胸的样子。肩生双翼,脊背呈连珠状,身体重心位于前部。身后均拖有长尾,尾巴粗大,始自臀部上方凸出略向上翘的根部,随后部分自然下垂,向后外括,略呈成“C”字形。尾巴以阴线刻的兽毛分作四段,独角兽的尾部最下一段则未见阴线刻,打磨光滑。它们尾末皆直抵底板,在四爪足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增强稳定性的支点,5个支点一起落于长条形底板之上。
两兽四爪足,各自的右前腿、右后腿皆向前迈,左前腿、左后腿则蹬在后边起到主要发力和支撑的功能。腿部肌肉矫健有力,姿态结合着上半身,整体显示出一种不疾不徐、雍容肃穆的王者之风。
天禄、辟邪的传承
有貔貅别名天禄、辟邪的说法。“貔貅”一词在汉代也已出现,如《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但在古代似乎并无明确将它与天禄、辟邪相联系的记载。至于今日常见一种雕作狮形、寓意吉祥的玉饰,被称作“貔貅”,它是否与汉代的天禄、辟邪有关联?还有待考证。
可以确定为本文所讨论两种神兽演变而来的,是南朝帝陵的石兽,以及后来逐渐褪其神奇色彩、流于日常化的石狮。南朝继承了东汉陵墓中的天禄、辟邪制度,今南京地区多有发现这类石兽,它们较之东汉的技法更为精细成熟,少了几分曾经的古拙意味。而更大的变化不仅仅在于形貌,还发生在功能与被运用的场域中,根本之处在于从东汉威严无双的镇墓兽,演变成了后来生活中府宅门前的看门兽。这种变化自魏晋以来就慢慢发生着: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以来,本土的狮子艺术深受萨珊波斯文化影响,狮子形象开始增加卷发,身躯被犬化;尤其在胡风大盛的唐代文化中,这种趋势得以定型。
清代的门狮习俗格外流行,富贵人家的府门前必得搁置一对镇宅石狮。比如《红楼梦》里写府宅之盛,最不经意的一个细节是,黛玉和刘姥姥出场打量宁荣二府时,不约而同都望见了府门口的两个大石狮子。冷郎君柳湘莲也是,在他对贾府颇为决绝的思维印象里,倒还记得东府里有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这三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都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石狮。曹公手笔便是如此,从不肯直露,总把那番气象巧妙地隐藏于白描细节之下,令贾府老宅子那种久经时间与人事之后、沉淀淬炼下来的荣华,由石狮子一类的旁峰侧岭烘托超逸,才来得底蕴悠长而醇厚,与曹公的文笔一样,已至臻境。
清代门狮凭其精美入世的造型和高超细腻的技法,俨然成为传统狮子的典型标本。直到今天,石狮艺术都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对经典的门狮形象往往是一雄一雌,一左一右地并排蹲坐着,皆为卷发,颈项上挂有铃铛,瞋目怒吼,神态威猛,但皆已无角无翼。门左的石狮右脚踩绣球;门右的狮子可能左脚踩一幼狮,幼狮背倒贴石座、倒身四肢朝天、腹肚被大狮踩摩,一大一小狮子似在嬉戏,天伦之乐溢于言表……它们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于威严中延传着人情的温美。
上溯至东汉、流传至今的石狮艺术,在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推陈出新、保持着生命活力。最初由异域传入、融合了本土文化,诞生出天禄、辟邪,而后持续不断地兼容并包;并自墓茔转换到滚滚红尘之地,如今依旧在镇守门宅、保佑阖府安康。它们以这种静默不语的姿态,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为人们展示了一个陌生又亲切的、与我们民族记忆根脉相连的精神空间。
(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及网络,侵删。)
“黑神话:悟空”主题艺术展|为情怀更为艺术
古人那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印章
故宫特展来了!172件文物感受希腊克里特岛的神话
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之美”)
越剧《红楼梦2025版》舞台版和电影项目启幕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守宝人丨云端守寺三十载
贵州:油菜花海绽春光
中转式旅游:追求“高性价比”与“松弛感”
蛇年寻“蛇”—— 藏在山西博物院里的“蛇”
“冰雪热”遇上“非遗热”,真燃!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理想的都城,秩序的杰作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相关新闻
当代紫砂发展创举 仿青铜紫砂壶专家品鉴会在京成功举办
2020年7月23日,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健康发展,“以工匠之心•致敬文明——仿青铜紫砂壶专家品鉴会”在北京华夏珍宝博物馆举行。
五十年代的张大千与傅抱石:一追摹唐人,一壮游写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大千侨居巴西时追摹唐人作品开创了新的泼彩画法的《仙山楼阁》、傅抱石壮游写生的系列画作、董其昌的二十页曾被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书画合璧山水小景册》等近日将在嘉德春拍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