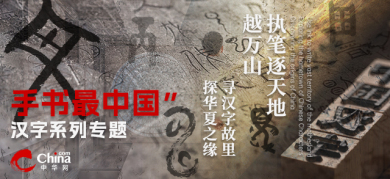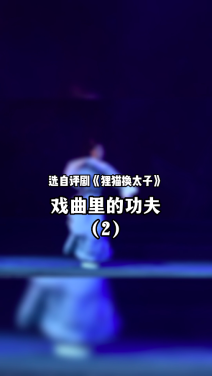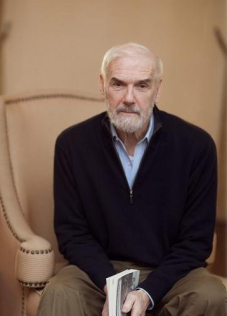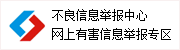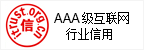创造我们自己时代的“现代”

王晴飞,生于1980年,江苏泗洪人。南京大学理学学士、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任职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文学论文集《望桐集》等。

周明全,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现任《大家》杂志主编。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等;与陈思和共同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
“此人之肉,彼人之毒”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这几年,你从社科院到刊物,最后又落脚大学,短短几年,在三个城市,从事了三个不同的职业。这几年的情况是,很多大学老师到刊物工作,如《当代作家评论》的韩春燕、《小说评论》的王春林、《扬子江文学评论》的何同彬、《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等,我自己在刊物,也觉得在刊物蛮自由的,你为何从刊物去大学?
王晴飞(以下简称王):这个怎么说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吧。此人之肉,彼人之毒。对于我来说,人生最理想的职业是大学教师,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各自的际遇,也会有各自 的困难。世界并不是为某个人设定,最理想的未必总是可以立刻实现,而且有的时候经历了各种情况,也不知道自己“最理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下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每个人的我之为“我”,也往往不是自己最初期待的结果,而是在不断地选择与被选择中逐渐成为的那个“我”。从刊物到大学,于我个人,是夙愿以偿,了解我的朋友多数也都是拍手称快,拍案而起,认为我终于从短途车坐上了长途车。对于这些理解我的朋友,我是心怀感激的。
如果撇除外界的因素,我是懒得变动且执行力很弱的人,有时候身处并非自己理想的境 遇,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做出大的改变,因为实在怕麻烦。而且我也觉得人生似乎并没有“最 好的”,有次好的就已经很不错,所谓的“好”,往往只是在我们既有的选择中让自己觉得更 适宜也更适意的。所以有时我也会感激人生中那些不可控因素,甚至是一些不大的挫折(挫折要有,但不要太大,不然 game over ,就没得玩了)。如果人生一路顺遂,本科毕业读硕士, 硕士毕业读博士,博士毕业去一所大学教书,一直到六十岁退休,那我可能不会遇到很多风景。有时候恰恰是一些当时看来“不顺”的际遇,赋予人一些预料之外的东西,让人生变得有意思一些。
周:多在一些岗位上体验一下,对从事文学研究也是好事。工作环境的变化,对你的研究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吧?
王:首先环境确实是有了变化,而我也确实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之前的大学经验,是学生眼中 看到的大学,而学生眼中的大学和教师眼中的大学, 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表达对大学向往的时 候,会有长期任教于大学的朋友泼冷水,给我对大学 的浪漫想象降温。不过说到对研究的挑战,我倒也并没有觉得很 大。大学教师真正需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教书,一是研究。在大学教书,于我确实是一个新经验,不过 我也很乐于去学习怎样教书,而且我总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似乎我天然就适合教书。人在做有价值的事时,总是会有更大的热情。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可以参与并看到事物的生长,做研究 会看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在慢慢生长,教书则看到学生的慢慢生长,这都是很让人快乐的事。人生有什么比做快乐的事同时还顺便解决了谋生问题更好的呢?
周:工作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研究方向的转变,毕竟要适应大学的考核方式。你到大学后,研究方向上做了哪些调整和规划?
王:工作环境的变化,确实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上,影响倒并不大。大学的考 核方式确实会更细碎一些,但是说到大体,其实与科 研机构并没有本质区别,大家的标准其实都是那几个,课题啊、论文啊。而且考核方式主要体现在成果的形式或刊发的载体,而不在内容,我研究的内容和兴趣不太会因此而变化。当然,也可能是我本来就疏于规划,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以后(过了 四十岁以后,确实会感到,留给我们的有效工作时间 其实已经不多了)。目前而言,我会较多留意当下比较有创造性的作品,也会关注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想多了解一些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情感与想象模式。大学给个人研究或知识结构带来的变化,会体现在讲课上。比如,为了把问题给学生讲清楚,会对以前泛泛阅读的作品或问题仔细研读,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以前忽略的问题。当然我讲课时间尚短,这样的时候有,尚不太多。作为一个中年人,我并不预期会有完美的环境,我也认为无论环境怎样,人活在其中,都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度,人和环境是可以适当互动的。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尽量让自己的兴趣、个性与环境之间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但如果外界标准实在让自己不舒服,那就舍弃一部分标准吧,只要自己的选择和内心自洽,就可以获得愉快与宁静。我也不太相信没有个人兴趣、热情的学术会是好的学术。人们经常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但是“出溜”真舒服啊, 我当然不是说人应该“出溜”下去,混迹于“心理 舒适区”,但是面对和自己个性或兴趣过分犯冲的标准,偶尔“出溜”一下也是可以谅解的吧?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对“标准”保持忠诚。
周:心态好,把一些事情看淡点,人就更轻松自由了。去年年底和陈思和老师谈批评家的出道问题,陈老师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如客座研究员制度、“今日批评家”等)几乎都是面上出道的几个发力点。当时他建议我“要从更加广泛的学术传承背景上去讨论,从价值取向的变化中找出这一代批评家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的状况,学院体制对他们的批评事业的干扰,以及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我觉得陈老师的建议非常好,你之前在社科院工作,后来又到刊物,在不同性质的单位工作过,现在在大学里工作,你觉得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有哪些干扰?
王:对于这些方面,我的感受其实有些迟钝,这可能跟我总觉得自己不在学院中(我确实时常会隐 隐觉得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学院”,但 有时候又觉得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 也不专心致力于做文学批评有关,我也觉得人应该跟某一 种被便宜性命名的整体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很少思考批评家群体该如何或者会如何的问题,偶有思考,也是会想作为个体的“我”在既定的环境或者 说体制里怎样尽量做得好一些。所以我所说的只能对我个人有效。至于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的干扰,我想这里想 表达的或许是指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外部的,文学批评这项工作在大学学术体制里的重要性会低于 文学史研究,不会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文学批评文 章不被计入考核成果,这虽然只是外部问题,但是成为一种学术风气或潜在的对学术价值的判断,可能 会引导青年人学术方向的选择。一是内部的,就是 现行的学院体制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理解, 会有一个相对的延后,所以有时候会显得停留在比 较陈旧的知识体系和观念里。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说起来可能没什么意思——很多事从个人角度说都会没什么意思,也没 什么道理——那就是学院体制对我没什么干扰。我 愿意把学院的作用理解为更专业的,更沉潜的,不轻 易被轻浅的风气裹挟的一种气质或者说方法,而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坚硬、更封闭、更保守的。在这种方法之下,文学批评会在文学文本与文学理论、文学现 象与社会现实、个人趣味与文学原则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和有益的张力,使两端互相激发、创造。对“学院”这样的理解,或许会被认为过于理 想化,但是个人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只要你自己相信这一点,也往这方向努力就好了。至少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它是可以实现的。而给学院赋予某种 狭义的内涵——正如我们所见,可以是完全相反的 内涵,且各有道理——并从而支持或反对它,是容易的,但我更愿意想的问题是怎样使“学院”于我们 自身对于文学的理解有益。
周:你这些年阅读量很大,但文章并不是很多,你是有意放缓自己的写作速度还是有其他考虑?
王:说来惭愧,阅读量大恐未必属实,写得少确 是无可抵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绝无有意放缓速 度或其他考虑,甚至我也很羡慕那些手快的朋友。倾尽全力都不敢说做得够好,哪里还敢保存实力?写得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懒散,所以经常是“半 年不开张,开张管半年”,尤其是写完一篇比较用心 的长文之后,会沉浸在劳作后那种充实的喜悦中,可 以躺下来看几个月的闲书而不至于产生负罪感。另 一个原因则是我很少去规划自己,兴趣上喜新厌旧, 所以很多觉得好玩的题目,在研读一段时间之后,就 会放在一边,而被新的题目吸引。当然“新”和“旧” 是相对的,因为“旧”话题被搁置后,过两年或许 又会被捡起来,成为“新”话题,继续做起来。所以有时候跟朋友聊天说到我的某篇论文,我可以毫 不心虚地说:这篇文章,从动念到完成,花了 x 年时 间。(x 可以是 2,也可以是 3 或 5)。因为确实从动 念后有三五年就没有再看过。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 习惯,因为重新捡起来的时候,要把冷灶烧热,关于 这个题目就需要一个新的“预热”时间。当然,从 正面来说,有时暂时搁置也是因为觉得准备不足,就 不强行去写,而是先放一放,等着它慢慢长大。而一 个题目一旦动了念,即便平时不去专门搜集材料,在 看其他书或闲览的时候,与之相关的内容,也还是会 自动从纸面浮现出来。所以有时候一篇文章一直觉 得没有把握去写,但是某一天看到某一本书,或是某 一条材料,忽然就觉得可以动手了。当然,顾随教人 写作,说到“巧迟不如拙速”,这句话我也常记在心, 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不必过于求全,不妨稍微写得快 一些。
周: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王:突破肯定谈不上,我目前不太去想一些特 别整体性的问题,即便涉及整体性的问题,也多是 从局部入手,小题大做——我总觉得自己对局部的 了解还不够。当然这也是我需要克服的问题,因为 实际上总体和局部的了解应该是相互作用的,我们 不太可能先穷尽所有的局部再去了解整体(实际上 也不存在一个既有的整体),也不可能先充分了解了 整体,再去研究局部,只能是大概有一个整体的轮 廓,以这个轮廓去大致确定局部的定位,同时在对局 部的研究中调整对整体的认知,这个过程是无尽的。所以我想我也应该慢慢试着去研究更“整体”一些 的问题。我平时的阅读和研究不是很有明确的整体 目标,多是随着兴趣读相关的书,解决自己对世界认 知的一些困惑,属于日拱一卒型。所以我这十年所 做的工作,谈不上突破,只能是说为将来的突破做准 备——假如将来会有突破的话。如果说这十年有什么变化或者说进步,我想 是慢慢懂得如何阅读、理解以及评论文学作品了。2015 年我们聊过一次,那次我说到我更多地研究的 是死人,而很少研究活人。所谓研究死人,其实是文 学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活人,指的是文学评论。二者 虽然有相通之处,毕竟还是有所不同。2014 年以后,由于外部的原因,加上随波逐流(如果用褒义词,也 可以说是随遇而安)的习性,我较多地关注活人,阅 读了比较多的当下作品,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更多地 懂得了如何切近新鲜的文学作品。
“‘虚’心涵泳,充分体味作品自身”
周:我看你近年的文章,对当代作家的关注较多,其实每位从事文学批评的从业者,都有自己偏重的作家。你比较喜欢的作家是哪些?或者说,你一直集中关注、跟踪研究的作家是哪几位?
王:对,近几年我确实对当下作家的作品关注得多一些。不过也没有特别集中关注或跟踪研究的作 家,我想我的阅读还是以“我”为主,在日常阅读中 发现能够吸引自己的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作品,会 停下来仔细研读,而不太会刻意追踪某一个或几个 作家,所以说不上哪些是特别偏重的作家,因为毕竟 发生在当下,文学的演变如流水,充满不确定性——当然,当下最大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无法预测的不 确定性——下一部能够吸引到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其实无法预测,也充满偶然性。我只能说近些年我 认真评论过的作家如刘亮程、朱琺、石一枫等,都是 很有意思也值得关注的。当然,没有评论过的作家, 并不代表我就觉得不好,因为评论也是和个人性情 有关的,有的作品很好,你也知道很好,但是与你的性情不合,你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充分理解它;也可能 其实有意评论,但是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谈论方式,或者觉得准备还不足,也会暂时搁置,但会一直关 注。而且那些没有被谈论的作品,也并非不存在,它 们隐藏在每一篇文章的背后,作为背景,制约着我们下笔的分寸。
周:近年,你写过两篇关于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对贾平凹的写作多有批评。对贾平凹或他们这代作家的评价,往往有两极化的现象,他们同辈或稍晚一代的批评家,对他们的写作基本是持肯定的,而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则对他们的写作有诸多批评。你认为这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的人审美”有关,还是年轻一代的审美更加自觉化?
王:这个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我 一直在批评贾平凹老师,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偶然性。最初好像就是因为很偶然的因素,写过一篇对贾平凹的写作提出质疑的文章,后来就决定再也不写了。之所以决定不写,也不是觉得这样写不对,而是我觉 得应该有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事要去做。但是这个 世界是这样的,质疑的文章有时候会比肯定的文章 传得远(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于是大家 知道你写过批评某位大作家的文章,下次编辑想要 这方面的稿子时就会想到你(毕竟你是熟手),而来 约稿的编辑又往往是好朋友,不好意思推托(比如 有一篇就是你逼我写的),于是就又写了一篇,这样 就会被一步步套牢,我给人留下的可以写批评某一 位大作家文章的印象就更深了。这样说,似乎有推脱责任的嫌疑,实际上既然 答应了约稿,自然是文责自负,因为答应了就是觉得 可以写也应该写。不过我不建议给“批评”或“表 扬”赋予过多的伦理内涵,比如我们可以认为爱“表 扬”的评论家是厚道的,也可以认为是拍马屁的,我 们可以认为好“批评”的评论家代表了良知,也可 以认为是哗众取宠。这些两极化的判断都可能是对 的,也都可能是不对的,凡是一件事“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就说明我们的思维已经走在了错误的 道路上,问题的根本一定不在这里。文学应该批评(狭义的批评)还是表扬,我认 为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甚至这样的一种两分法其 实会模糊了文学批评的真正意义。文学批评不是要 去夸一个作家,或是去骂一个作家,而是要进行一种 有价值的创造。我们在阅读之初,自然要尽量排除 先见,“虚”心涵泳,充分体味作品自身,在此基础 之上才能做出论断。应该是先信后疑,而不应只疑 不信,或只信不疑。信才能得其大体,疑才不会在文 本中迷失自己,被作家牵着鼻子走。如果预先悬置 一个“夸”或“骂”的目标,带着这样的目标去阅 读作品,自我就不会真正打开,“我”与作品也没有 形成有效的互动,很容易只看到自己需要看到的东 西,而不能对作品有整体的感知,“我”在阅读过程 中也不会有任何成长。“小心假设,大胆求证”,这样 的话从字面上来说当然没问题,但事实上人在有了 既定假设之后,求证时自然就不免向假设靠拢。当 然,我现在决定,以后轻易不再写批评贾老师的文章 了。这次是认真的。至于不同时代的人对贾平凹作品评论的两极化,我以前倒没有特别在意,如果有的话,我想这里 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如你所说的,不同年代的 人,在审美上有差异;二是我觉得作家的作品也在变 化,老一辈的评论家可能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 所以评论新作时总不免带有早期的阅读体验和审美 判断,而年轻的评论家可能更多看到他的新作。不 过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也可能在于文学之外。现在 的评论很多时候是人情或任务。所谓人情,指的是 大家都有交情,写评论常常会成为捧场或支持。我 们现在流行“小伙伴”,老一辈自然也会有他们的“老 伙伴”。所谓任务,指的是写作未必是自己内心真实 情感和态度的流露,而只是为了多一篇文章,用于评 职称或完成考核。论文只是谋饭的工具——我从来 不反对写文章可以谋饭,但不应该仅仅是谋饭。这 样的评论,其实是可以量产的,因为大家好歹都是读 过博士、硕士的人,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文学理论与 文学史知识,最擅长的就是花式夸人,可以说几乎没 有夸不了的人。只要给个角度,把腹中的知识堆积 上去,就会是一篇论文。尤其是贾平凹老师特别体 贴,他的每部长篇小说都有一篇非常用心的后记,在 后记中,他会手把手推心置腹地教你如何正确阅读、 理解、阐释他的小说。评论家只要按图索骥,照章发 挥即可。所以我们的时代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作家会非 常希望自己被评论,我也见过很多作家抱怨评论家 不够关心他(不关心的表现就是不给他写评论),但 如果评论是一种含有情感和态度的创造性工作,那 我想作家面对评论的态度也会严正慎重得多,不会 像现在这样轻松乃至轻佻地要求自己“被看”,因为 你真不知道这群评论家会说出什么话来——但是现 在,他会预设,评论就是捧场。而且谁夸我我就觉得 谁说得好、说得对,这本就是人性。至于我们这代人是否比老一辈更审美自觉化, 我也没那么乐观。从知识结构上,我们这代人,在专 业知识方面,可能会更完备一些,因为赶上了好时 代。但是也因此,我们的评论可能也会更单一,因为 都被局限在相似的专业知识里,一方面是专业化程 度加深,一方面是广度上反而未必赶得上前辈。大 家经常说的同质化其实就源于这一点。大家读着同 样的书——也因此少读专业以外的书,有着差不多的经历(本科—硕士—博士—高校或研究机构),在 对人心、人性的理解上其实反而可能不如我们的前 辈。而且如前面已经说到的,老一辈有老一辈的“老 伙伴”,我们也有我们的“小伙伴”,在人情方面大 家也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年轻一代未必比老一辈更 自觉。
周:之前听你多次谈起网络文学,尤其是你谈网络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存在某些关联,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几乎没关注过网络文学,根据你的阅读,你认为网络文学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王:我确实读过不少网络小说,一度甚至颇有沉 溺,尤其是两次手术后养病,因体力不足,注意力不 能集中,更是看了很多网络小说,既算是过了网瘾, 也算是一种休息吧。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目前网络文学的发展,尚 属于群雄并起的草莽时代,虽然也孕育了不少新的 可能性,但还只能算是出现了陈胜、吴广,而没有刘邦、项羽——所以才会遍地“大神”。我想至少要产 生类似于武侠小说中的金庸这样的作者,作为类型 文学的网络小说才算是真正立住了。而且我们对网络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也为现状所 限,仿佛网络文学就只能是小说,而小说又只能是类型文学,甚至爽文。我想在网络文学出现之初,它其 实倒是反套路的,甚至可以说是先锋的,当然也不乏类型文学(毕竟最早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是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但是并不像现在这样在资本 的驱使下,类型文学一枝独大。现在的网络文学看 似繁荣,但只体现在作品和读者数量上,从文学的品质和品类上看,是狭窄的。“网络”是一种新的生产 和传播方式,这种新方式会影响“文学”呈现出来 的样貌,但并不必然排斥所谓的“传统文学”,也不 必然排斥小众和严肃文学。但我也相信,随着那些 与“传统文学”相比有真正异质感的可能性的发扬光大,“传统作家”迁移到“网络”,网络文学的前景 是阔大的,不会再简单地只是加一些“网络”元素 的“传统文学”的低配版。所以,可以说我对网络 文学的现状评价不高,但对网络文学的未来很看好。至于网络文学和古典的关系,当下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古典文学修养很好同时也着力借鉴古典文学 符号、情节和方法的网络小说,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与其说是网络文学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毋宁说它是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而实际上类型文学、通俗文学都不免跟传统文化藕断丝连,因为中国人的情感与欲望结构,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而对于多数网络作家,传统文化也只是作为碎片化的标识点缀在作品中,以期唤起读者熟悉的情感想象模式,他们并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传统。
周:你有一段时间很迷恋古典文学,集中研究过一段《聊斋志异》,当时还准备就此写一系列文章。你是如何看待古典小说的?它们在今天还有哪些意义和价值?
王:确有此事,不过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去写,所 以看了两遍,最后只写了一篇关于汪曾祺改写“聊 斋”的文章。这也出于一种考虑,就是不必跨界太远, 虽是说“聊斋”,但也是在说汪曾祺,毕竟所学专业 是现当代文学,把话题拉到专业内,比较有底气些。至于古典文学或者说古典文化著作,我确实一 直很有兴趣阅读,这不是出于具体研究的需要,而纯 粹是觉得有意思,也是觉得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应 该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来路。说到这里,我会想到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或者 说评价中国传统文学。在“五四”时期,新文化派 和守旧派在文化上是对立的,也各有道理。新派—— 比如胡适——会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已经不能 适合新的时代,那时候紧迫的是“现代”,是让中国 进入“现代国家”之列,是让中国人先生存下来,所 以他们会以“求同”思维看中国传统,认为传统文 化乃至汉字不能与世界相通,不能合于“现代”的“普 遍”,所以需要被淘汰。而守旧派——比如刘师培(其 实还包括属于新派的周作人,看出了文化断裂的复 杂性)——倒是“求异”思维,会认为恰恰是那些 与“世界”不同的部分,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本,才是 中国文学足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理由。到了今天,中国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 历程,虽然挫折不断,很多地方虽不能说是已经“足 够”现代,但是“现代”也的确深入人心,我们面对 古典文学的态度和判断,也的确应该与“五四”先 哲有一些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五四”的背叛, 而恰恰是继承——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认识自己的 时代使命,面对自己时代面临的问题。当然,我们说的“现代”,固然是来自对西方的借鉴,但也并不存 在一个现成的“现代”可以直接拾来,我们的“现代” 只能是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对我们的问题和处 境,结合我们的传统,创造出来。日本艺术家冈本太 郎有一本书,书名即是“传统即创造”,传统需要创 造,现代更需要我们的创造。而古典文学在今天的 意义,我想是可以使我们在“现代”的路上越走越 远时,以过去的“经典”来作为镜鉴,参与“现代” 的创造,当然,在“现代”之眼中,“古典”也会再次“创 造”,洗濯出新的意义与价值。如果“古典”只是古 人认识的那个古典,它对于我们现代人就没有意义, 我们今天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如“学衡派”、林纾, 多有恕词,甚至去发掘他们的价值,绝不是因为他们 是正确的,而恰恰因为他们是失败的,他们只有失败 了,才有被重新发掘的价值。
“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
周:2015年,我们对话时,你在谈批评观时说过:“我们只有了解胡适,了解周作人,甚至了解学衡派,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鲁迅。对于他们的研究,当然会给我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观,而这种文学观有助于我在评论当下文学作品时分寸的把握。当然,文学观过分稳定、单一是很危险的,我相信最好的状况是在持续的阅读、思考中不断地微调自己的文学观,使自己能够更多地向新鲜、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敞开,而不至于过分抱残守缺。”七年过去了,你的阅读和思考更加深入了,批评观也相对稳定了吧?这些年你的阅读和思考、写作,你所秉持的批评理念是什么?
王:我关于批评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如 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我对于你上面所引的这段话 理解得更深入了一些,有些在以前悬为理想的目标, 现在觉得似乎可以比较踏实地触摸到了。当然,看 到朋友引用自己多年前的文章里的话,心中是有点 惴惴不安的,因为如果现在觉得之前的说法很幼稚,会觉得羞愧,就像看到自己儿童时的照片;如果觉得 之前的说法很好,就更羞愧,因为这说明这些年的学问没什么长进。
周:在《“业余”的批评及牙与胃的功能》中,你谈及:“在我们与文学世界之间,就隔着一个文学理论的鸿沟。这些文学理论与文学术语,成为我们阅读、批评文学的视角。但正如狂奴欺主,工具也会反客为主,束缚文学阅读者的眼光,就好像望远镜本是要人看得遥远,显微镜是为了观察得精细,只用望远镜和显微镜则不免管窥蠡测,只见一斑。文学理论和文学术语也会变成文艺黑话,限制我们看到第一手的文学世界。过度依赖文艺黑话的评论可以用一个函数公式来展现:f(x)=y。x是作品,f是文艺黑话,y则是评论文章。只要将作品源源不断地放入文艺黑话的算法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文学评论产生出来。当然有时候f也不仅仅是文艺黑话,也可能是某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这样的评论是可以批发,并且立等可取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过多地使用理论或理论缺失,可能都是问题。那你认为,文艺理论和文本解读,它们应该如何平衡,才能更趋于合理或完美?
王:这句话开了点玩笑,甚至故意用了个函数公式,不过意思还是认真的。文学理论在今天我们对 文学的理解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不懂文学 理论就不可能懂现代文学,在你所引的这篇短文里, 我还说:“直接与现实狭路相逢,赤手捉蛇,固然是 一种本事,可是放着现成的桥不走,偏要去泅水,也 不免迂执……”现代文学与现代理论之间是相互浸 润的关系,靠天然的直觉和体悟,不可能真正懂得现 代文学——而实际上,处在现代的文学语境里,也不存在不被现代理论“污染”的直觉。不过理论的使用,要有其适用性。理论有其深刻性,也有其抽象性,当它与具体的文学作品遭遇 时,需要有一个相互的激发,而非可以即拆即用;我 们日常用到的文学理论,多来自西方,这些理论是从 西方文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移植到中国,自然要 有一些变形;具体到使用理论的个人,也会各有天 性、才情的差异,有的人适合耍大刀,有的人适合用 绣花针,也并不是只要理论好,就一定适合每个人。最为重要的是,不论理论如何重要,最终和文 学文本短兵相接的,是有理论素养的“我”,而不是 理论自身。所谓文学理解、文学批评,都应该是“我” 先真正懂得了“理论”,然后“我”去阐释文学,而 “我”与文学的交融搏斗,也不仅仅是对静止的理论 的使用,而是在创造理论新的内涵。理论也只有在不断的文学评论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完成。如果“我” 确实懂得了理论,而又能真正在文本中悉心涵泳,那 评论呈现出来的就会是一个完整圆融的样貌,而不 是所谓的“两张皮”,就好像我们吃了各种食物,最 后都变成力气,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不 是各种尚未消化完全的食物。
周:在《“业余”的批评及牙与胃的功能》中,你也谈及:“在阅读上要尽量做到‘牙好,胃也要好’。牙好,可以嚼得动;胃好,可以吃得进。只有广泛涉猎,才能造就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全的人格,兼有趣味的综合与理智的分析。”在今天这种庞杂的知识生产下,要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广,也很难。或者说,太广似乎也会影响到专。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批评家涉猎的领域很广,但似乎似是而非的东西又很多。我知道你的阅读是很广的,在广和专之间,你是如何平衡的?
王:如前面我们聊到的,一件事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说明我们的思维已经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比如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强调哪一方面都可以,但也都有缺失。其实广博和专精是在同 一个方向上的。如你所说涉猎广,很容易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不可能算得上真正的广博;而致力于“专” 可能视野狭窄,视野狭窄又如何能避免一叶障目而有真正的专精呢?专精一定是建立在一定的广度之上的。没有一定的整体感,我们对于部分,不可能做 出真正精准的理解与评判。而没有精深的研究,所 谓广博,其实不过是碎片化知识的拼凑,甚至是茶余 饭后听来的耳食之言,这样的见识出租车司机会超 越我们,百度更会超过所有人。所以广博与专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做到也确实难,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我想可以设 定有范围的广博,而且所谓广博,起码要达到“高等 常识”的程度,而专精则也不宜限制太窄,可以适当放宽,这样不至于坐井观天。当然,最重要的是多深度阅读,有足够多的深 度研读,专精与广博才会平衡得更好。所谓“一力降十会”,就像练武功,如果力量达到了,很多本来使不出来的招式也使得出来了,很多本来需要费尽心 思平衡的两难问题也就不再是两难了。之所以有很多 两难,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读书太少,力量太小。当然 这也是理想境界,我们可能永远都达不到类似于钱锺书那样的阅读量,我本人也平衡得不好——不然就不会出现你前面问的为什么写得太少的问题,但是我很向往读书上的“大力者”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周:近几年,年轻批评家似乎都有一种“出圈”的冲动,除了专业外,广泛参与到文化领域,甚至是偏娱乐的圈子中去。但你是少有的一直保持定力的年轻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年轻一代部分批评家的“出圈”现象的?
王: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 得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批评家以个人身份参与到圈外领域,是 个人自由,更无伤大雅,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甚至 一个优秀、有趣的人出圈,会让更多人看到有趣的人 与事,倒是群己两利的。在这个层面,我们要注意的 反倒是出圈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要能够把本“圈” 内真正好的东西带给更多人,到了别的“圈”,也要达到该“圈”的及格线。毕竟要出圈,其实是能同 时跨过两个圈的门槛,而不能因为我们有“批评家” 的身份,就要求别人对我们“低标准、宽要求”,不 能因为自己是“外行”,就真的“外行”。举个例子吧, 我想如果能像易中天那样,让更多的人喜欢文学与 历史,其实也是有功德的。其次,作为一门学科,或者说一个行当,如果常 有“出圈”的焦虑,以不能“出圈”、未能被更广大 的人群知道为憾,这是不成熟的。那很可能说明这个行当还不成其为一个行当,这门学科也还没有成 其为一门学科。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研究相对论 的人会遗憾懂得相对论的人太少,甚至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有另一种心理,会以自己的研究被更少人 懂得为荣。我们在看科学家的轶事时会发现这样的 自得:全世界懂得量子力学的人只有三个,而“我” 是其中之一。一门学科有广大影响,于社会有益,是一回事,这个行当的从业者以知道自己的人数多寡判断优劣,是另一码事。最后要说的一点,就是不论有没有出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要出圈,先要在圈里。陈寅恪在谈论学术时,曾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 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我 们可以移来说“在圈”与“出圈”。我想一个学者, 首先要“预流”,然后才谈得上超越潮流;同样,如 果要出圈,首先要在这个“圈”里,先要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做好,在此之上才能谈得上“出圈”,把 本来只为“圈内人”能领略的美好风景带给更多人, 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曾在圈里,那还说什么出圈呢?那不叫“出圈”,那是没入门。
周:若给批评家朋友或晚辈推荐几本书,你会推荐哪几本?
王:推荐书,就像开药方,要针对对方的症状和 需求,而且我很少觉得会有一本或几本书让人读了 会立刻就能掌握某种秘诀或法则,像武侠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获得奇遇,修炼了某种绝世武功(比如降龙十八掌或易筋经之类),一朝登天,走上人生巅峰, 我们不论是要更多地理解这个世界,还是掌握一些阅读、理解、阐释文学的方法,都需要大量地读书阅世,甚至在读书较多以后,很多“烂书”也会从反面 给我们以启示。所以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其实是躲懒,偷换了概念,糊弄了过去。这次我想如果非要推荐的话,就推荐米兰·昆德拉的《帷幕》和《小说的艺术》吧,倒不是说这两本 书就一定比其他谈论文学的书更好,只是它们在我个人关于文学理论的阅读中,是最早对我的文学理 解产生很大冲击的。
周:谢谢晴飞。
推荐阅读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连日来,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走出去”,对外精准推介燕赵文旅资源、签约合作项目、开拓文旅市场,海外“朋友圈”动态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据了解,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街区将文化、体育、娱乐、艺术、教育与生活等业态充分融合,并结合周边配套设施举行文体活动,很受年轻消费者喜爱。此外,首店、首发、首展、首秀等也增添了这里的吸引力。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举办,“南腔北调”在此交流展示,戏曲名家带来精彩展演。本期我们约请参与百戏盛典的戏曲人才和相关从业者,就戏曲人才培养、濒危剧种保护、创新传播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为繁荣中国戏曲百花园建言献策。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白族扎染的工序多达10余道,其中扎花和染色最为考究。扎花考量技法的精致度,染色是通过天然染料染出不同颜色,十分考量技术和经验。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历经19天的精彩演出,9月23日,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志纯宣布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8月20日,国产首款3A(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上线,一经发售,相关词条迅速登顶海内外多个社交媒体热搜榜单,持续刷新在线玩家纪录,带动众多相关取景地关注度翻倍,中国外交部甚至也回应其热度……“悟空”彻底“出圈”。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银饰在苗族人生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按照苗族习俗,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要“打三朝”,亲朋好友在这一天带着礼物前来祝贺,新生儿将会第一次收到银制的礼物,蕴含着美好的祝福。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走进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纱縠行的三苏祠,秀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令人心旷神怡。这里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生活居所,南宋时将故宅改为祠堂,经历代修葺扩建,成为人们拜谒、凭吊三苏的文化圣地。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恰是处暑时节,人云:“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这是古人对夏末秋始节气的真实写照。是时,家家户户忙着修缮仓廪,以备丰收存储新粮。斗转星移,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年之中节气物候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