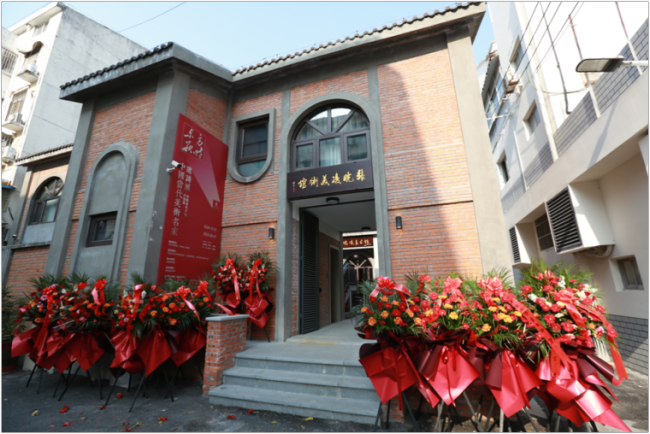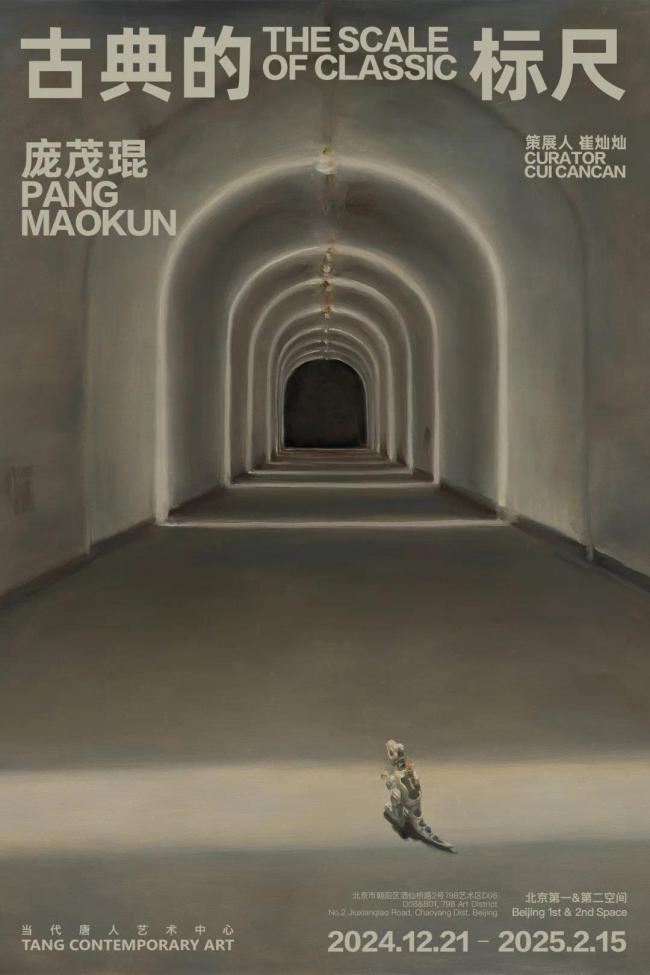坚持近30年,他用一只铅笔竟画出北京胡同的生趣和乡愁
深爱北京胡同文化的著名画家况晗和北京民俗专家陆原携手,用10年的时间打磨了近百幅技法独特的胡同画作,《树影鸽子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一书近日面世,一个饱经风霜的“胡同北京“就在眼前。

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帽儿胡同、东交民巷就在眼前这部书由一张张手工铅笔画和有趣的考证文字互相对照构成,讲述老北京胡同的历史沿革与当今日常生活生态。南锣鼓巷、帽儿胡同、东交民巷、西裱褙胡同、烟袋斜街、景山前街等一个个读者耳熟能详的北京胡同,在画家笔下充满灵动之气。

烟袋斜街
况晗说——
我画的不仅是北京胡同,更是北京的城市气质。人们被我的画打动,其实是被胡同打动。这些画的艺术性再高,也不及历史的永恒。
有些胡同,花了很多钱改造,但效果如何呢?我问过很多北京市民,他们不反对城市改造,但对具体的改造细节不乏保留意见。那些老宅子的主人看到我的画,再看看他们现在的房子,眼泪就出来了。

东交民巷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画故宫、长城、天坛这些高大上的建筑,却偏偏要画不起眼的小胡同?我说,因为那些建筑都是国宝,国家一定会保护;可胡同不一样,今天不抓紧画下来,明天就没了。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看完故宫也许会问,那个朝代难道只有皇帝,他的子民都住在哪儿呀?

北帅府胡同
陆原说——
北京是千年古都,在周朝为燕国蓟城,燕昭王为振兴燕国,受谋士郭隗“五百金买马骨”策论启发,筑黄金台招揽人才,留下了燕京八景之“金台夕照”景观。在辽朝为燕京,留下了天宁寺古塔,是北京现存最古的建筑物。在金朝为中都,留下了卢沟桥和大宁宫皇家园林即今北海公园。在元朝为大都,留下了通惠河和国子监、孔庙。在明朝为北京,留下了皇宫紫禁城。在清朝亦称北京,留下了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清漪园即今颐和园。

炮局胡同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古往今来,天南海北,家国情怀,梦里乡愁。有多少人杰俊才,踏着卢沟古道而来,乘着运河航船而去。他们为北京留下的痕迹,有的已随岁月飘逝,有的却是名垂青史。

石雀胡同
再看作者笔下的铅笔胡同,并非胜在如何逼真,最打动人的是这些作品背后透出的老北京随性、宽厚的精神内涵。铅笔朴素的线条、厚实的灰色调,最适合表现老北京的韵味——片片残墙的斑驳、砖石风化的质感、老槐树的光阴、胡同的年轮,画中处处可见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情绪、人的思想、人的故事。

松树街
写胡同要写出真相
每一个胡同的前世今生在两位作者的笔下,充满着特别情感——
花梗胡同南邻的东旺胡同,明朝旧称马将军胡同。往南的白米仓胡同,明朝旧称济阳卫仓,是济阳卫驻军的粮仓。南邻的府学胡同,因明朝顺天府学校而得名。元朝末年,有僧人在这里营建报恩寺,寺院完工还未及安放佛像,明朝征虏大将军徐达已经攻入大都城。僧人担忧寺院会被征用为军营,听闻明朝尊崇孔子,就去孔庙借来孔子牌位供奉在寺院,谎称这是新建的学校,于是弄假成真,寺院先是成为大兴县学校,后来又成了顺天府学校。
府学胡同在元朝有兵马司的牢房,南宋丞相文天祥在这里被关押四年。文天祥在这里写作了《正气歌》,序言写道:“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文天祥说牢房有水气、土气、火气等七种污秽恶气,但是我有浩然之气,这就是天地正气。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北平按察副使刘崧在牢房旧址建造了文丞相祠,并且将这一带街巷命名为教忠坊以纪念不屈的忠臣。文天祥所说的七种污秽恶气之一是“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可见北侧的白米仓胡同在元朝已经有了粮仓。

作者陆原
陆原写胡同坚持追求真相,坚持说有用之话。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民国时期书画家叶恭绰断定那是元代的塔,但让陆原特别有成就感的是,他通过翻阅、研读大量古籍,认为万松老人塔为金代所建,而非元代。
他解释道,砖塔是高僧万松老人的灵骨塔,通常都说是元朝古塔。但是万松老人生于金朝大定六年(1166年),卒于蒙古贵由大汗元年(1246年),终年八十一岁。在万松老人圆寂二十五年之后的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才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所以砖塔建造时间要早于元朝。

砖塔胡同
陆原写胡同也有自己的个性。况晗画了一个全聚德烤鸭店,陆原想,全聚德没有委托他做软广告,就没有写文字。还有老舍故居,他更是觉得无从下笔,人人皆知的老舍生平、评价,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复述。因此,老舍故居这幅画也没配文。
他们因胡同而结缘两位作者因对北京胡同的特别情感而走到了一起。陆原今年58岁,他自述出生于元朝大都路总管府所在地交道口,少年住在通惠河终端什刹海南岸白米斜街,青年住在明朝夕月坛东门南礼士路,中年住在金中都丽泽门旧址高楼村。

作者况晗
况晗是江西人,他199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画胡同已有近30年。“其实住胡同开始是很难受的。”况晗回忆,当年所住的胡同只有9.13平方米,一家三口吃喝拉撒全在这里,别说放置一画板,就连转身都得小心翼翼。
下班后,他常在门口吸闷烟,无聊透顶。时间长了,他发现泔水桶、垃圾桶在石榴树下和扫把、拖把一样能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这就是我画胡同的开端,当然我是用的老本行水彩画的。”况晗着迷于北京胡同的沧桑感,“北京砖墙胡同,砖缝里积的都是几百年的尘土。”

长巷二条
画胡同并非易事。多年前,寒冬腊月的北京有零下十几度,况晗几次在外写生,洗水彩画笔的水结冰了,常让他半途而废。闷闷不乐中他总是希望找到解决的方法,翻翻自己以前的速写,铅笔不用水、不结冰,工具还简单,一块画板,一盒铅笔,一个小马扎就OK了。况晗本想用此方法练习一下基本功,天热了再来画水彩画,但一画不可收拾,一直用铅笔画到现在,连他自己也不可想象。在况晗眼中,胡同的灰色与铅笔的铅色有了完美结合,这让他深感意外。

宣武门外大街
画胡同,写胡同,两位作者也见证着胡同的变化。况晗认为,北京胡同的变化最大的时候是申奥成功之后。申奥之前有的胡同脏乱差,他为收集素材拍照,居委会的老太太常常盘查。但奥运之后,游胡同的人多了,居民脸上那些怀疑的眼光也换成亲切的笑容了。

香铒胡同
况晗从1991年开始画胡同至今近三十个年头,他说,自己也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从对胡同的一知半解到如今也算是如数家珍,跑胡同画胡同更促使他的艺术获得升华。“我常常想起在我艰难的时候,胖大妈、卢大妈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对我这个外来人员的包容和帮助,小院的兄弟姐妹对我们一家人关怀备至,让我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有了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