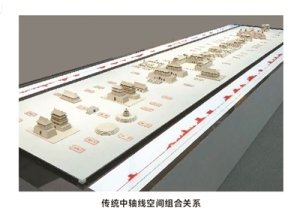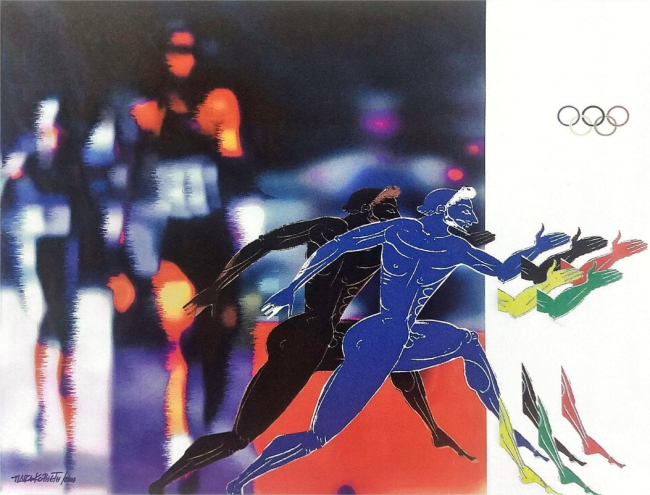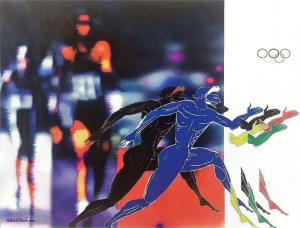民国第一才女张爱玲 蚤子还是海棠花?(7)
张爱玲在给朋友朱西宁的信中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在赖雅的引领下,张爱玲对美国逐渐熟悉起来。虽然,他们缺钱,但是却不缺爱。第二年过生日,她收到了来自丈夫精心准备的蛋糕和红玫瑰,以及亲手制作的肉饼、青豆和米饭。还有一年过生日,张爱玲和赖雅一起去看脱衣舞,看得津津有味。
可惜,这一段不多的温馨日子实在太过于短暂,如流星,在张爱玲的生命中一闪而过。
婚后不久,赖雅中风,难以正常写作,家庭开支全靠张爱玲卖文维持。她卖力地写过英文小说,却举步维艰,枉费所有努力。她干过翻译,写广播剧,当驻校作家,做独立研究等一系列糊口的工作。此外,她还要照顾瘫痪在床以至大小便失禁的赖雅。这在外人看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直到1967年,赖雅病逝,张爱玲照顾一个中风病人整整10年。往后余生,张爱玲一直冠着夫姓,称呼自己为Eileen Reyher。

张爱玲1966年于华盛顿
她在小说《半生缘》里写道:
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赖雅走后五年,张爱玲几乎与外界断了来往,在洛杉矶,开始了长达22年的幽居生活。
她不喜见人,不愿应酬,不接电话,和外人沟通只用纸条和简短书信,极力避免任何语言交流。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她很少出门,报纸也不怎么看,只是每天12小时开着电视,把音量开到极大,抵抗寂寞。
她晚年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怕虱子,怕痒,经常穿那种宽大的灯笼衣,头发都剪掉了,出门就包头巾或者戴假发套,并且为了躲跳蚤,开始疯狂地搬家。短短几年内,累计搬了180多次。
因为频繁搬家,她的生活用品也极简到令人发指。行军床,折叠椅,折叠梯,电视机,落地灯就是她全部的家具。她晚年的大量学术和翻译工作,甚至是趴在叠起的纸盒上面完成的。
当我们觉得她活得家徒四壁时,她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身外之物还是丢得不够彻底。”
当我们觉得她活得孤单一人时,她却花十年时间阅读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写了一本学术论著《红楼梦魇》。

张爱玲
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张爱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度声名日隆,外界再次将她捧红。她先是被台湾、香港承认,继而被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认可。两岸三地掀起了张爱玲文学热,世人对她的绝代风华惊叹不已,不少的学者都试图向她发起回国邀请。
只是这一切与张爱玲已经无关了,毁也罢,誉也罢,她已然是不在乎的了。正如19岁时她在《我的天才梦》里写的倒数第二句所言:“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西木区的一幢白色公寓内,房东发现206号的一位中国老妇人死了。
房东发现她的情形是这样的:屋里保暖的日光灯还开着,各种证件都收拾好了,放在门口处。她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头朝着房门,脸向外,遗容安详,只是出奇的瘦。
22天后,9月30日,按照她的遗嘱,亲友将她的骨灰撒向苍茫大海。
那天,正好是她75岁的生日。
自从1955年乘上去美国的游轮到1995年魂归大海,真是40年如一梦。
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说: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张照片,34岁摄于香港,照片中的她高傲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