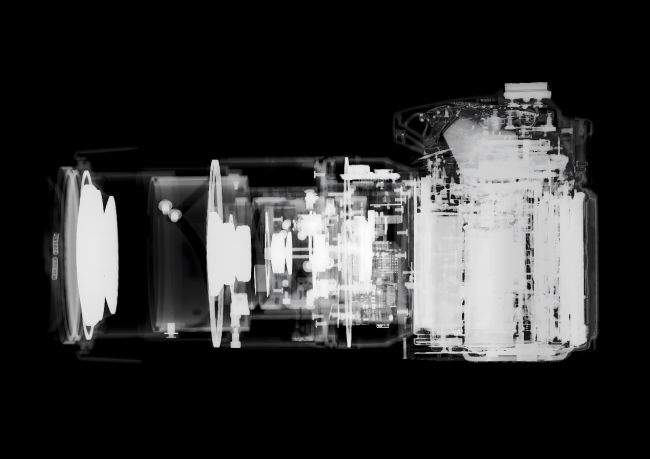回到傅雷的美术史(2)
生动者,是全书行文绝没有那种刻板的面目。仅前三讲,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历史认知就各有章法。谈乔托的绘画,是由圣方济各的宗教思想引出,思想变革与艺术变革相映;讲多那太罗的雕塑,则从艺术家一生几次重要的风格转型娓娓道来,主体强烈的创作理想成为叙事核心;而在详述波提切利之前,又先勾勒了当时佛罗伦萨艺术繁荣的盛况。叙述角度多样之外,语言的诗意化也是这部美术史著作的重要特色。优美的文学化的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如这段描述:
在《维纳斯的诞生》中,女神的长发在微风中飘拂,天使的衣裙在空中飞舞,而涟波荡漾,更打造了全画的和谐气氛,这已是全靠音的建筑来构成的交响乐情调,是触觉的、动的艺术,在我们的心灵上引起陶醉的快感。
这种行文风格让《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还具备了文学意义,它不仅使历史中的艺术作品有了鲜活的气息,同时还拉近了普通读者与艺术史之间的距离。这份洋溢的审美热情为这本书的“亲民”提供了契机,它超越了专业美术学习的圈子,为今天人们热切渴望的那种以完善人的修养与人格为重要目的的美育提供了养分。
这里似已涉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当代价值,不过我们仍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本来看待。
在序言中,傅雷说“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与历史者寥寥”,这说明他的确把自己的论述作为对一个历史情境的回应。在他写作此书的时代,中国艺术的未来道路像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其他方面的探讨一样,充满着革新的热情与建构的焦虑。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技法传入中国,但由于没在历史梳理中正本清源,常造成创作中肤浅的形式模仿。傅雷作此书,特强调中西艺术之别。“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生长。”(见《序》)傅雷也是丹纳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著作《艺术哲学》的译者,这句话看着便很有丹纳的腔调。但提醒时人注意东西艺术之相异,并非要阻隔东西调和,而是希望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艺术的历史源流,惟深刻之研判,方能为我所用。这种对他者文化理性的态度,是本书写作的重要基调,对理解彼时跨文化碰撞中的中国美术理论发展也不啻为一份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