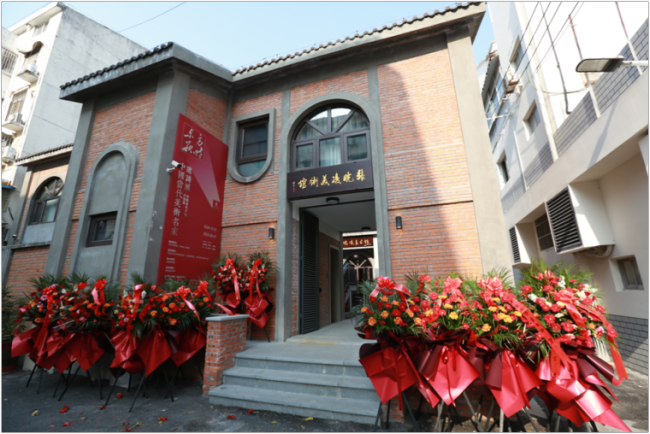崛起的中国水墨必将在世界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楚寻欢
文/楚寻欢
中国画沿袭至近现代面临的彷徨、冲突与变革
中国传统绘画史中,山水、花鸟、人物画成为三大主流画科,其中山水画早期因庙堂所仰而宏伟彰显,花鸟画最为文人遣意抒怀所喜,人物画则逐渐从宗教色彩浓厚的壁画转向抒发作者主观情感之凭借。不管是山水、花鸟抑或人物画,中国在野文人画对宫廷院体画的独立反叛精神推动了中国水墨画语言写意精神应时而变的延绵生命力。
纵观中国美术史,我们崇尚高古的宋元,更多是因为他们高洁出尘的逸格,这种轻器重道的艺术之路也是中国文人写意精神的情怀底色。
从宋代的梁楷、法常到元代的倪瓒,再至明清之际的担当、八大、石涛、徐渭,中国的文人写意画已经走至迄今为止最后一个高峰。

黄宾虹 黄山松谷龙潭小景 83.5×40.5cm 1953年
明清以降,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在传统一脉上每况愈下,略为出彩的是齐白石、黄宾虹二君。他们虽然在画格上逊于前人,但在语言形式上呈现了个性鲜明的自我面貌。其次,潘天寿雄强的“指墨”、傅抱石激情的“抱石皴”、陆俨少疏朗跌宕的“云水”也曾别出心裁地给我们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倡“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李可染其实最缺的就是“胆”,此种秉性也大大限制了其画格,他虽也试图对中国画的造型与明暗处理上融入西法改革,憾心手不能相应,“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却未能“用最大的勇气走出来”。与之相映成趣的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石鲁,传统笔墨奇佳,却锐意改革,遂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一代典范。有诗为证:“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为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林风眠、常玉、吴大羽、关良、丁衍庸及至后来的赵无极、吴冠中等在吸取西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段探索中国现代艺术走向国际的新征程。成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决澜社,是一块向“平凡与庸俗”挑战的艺术革命圣地。其时的上海是中国近现代艺术走向国际的桥头堡,也可谓近现代先锋与传统艺术交融最活跃的一面旗帜。应该说今天的上海同样聚集了不少向往现代艺术的海派画家,他们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性的绘画取向好过北方普遍装腔作势的假大空,但这种小资感觉层面的模仿毕竟是小道,在自我本体完善上还远未成气候。比如擅画戏曲人物的丁立人,虽然在构图形式上吸收了某些民间样式,但其笔墨语言上缺乏灵气与生机,这种偏于符号设计的自我复制在当下艺术市场渐成风潮,其症结还在于其文化底蕴的严重缺失。作为吴大羽的学生,张功悫与赵无极一样深受同门师友影响,在绘画语言上都深受西方“抽象”影响,可谓一脉相承,也保持了那一代人优良的为艺品质,只是在作品表现力上与吴、赵相比显然相去甚远。从印象派风景转入抽象领域如今还不能自拔的余友涵,实际是一种倒退。因为,艺术发展到今天,抽象艺术在西方已经是一种过去式,那么,中国有抽象吗?区区曾在《中国有抽象吗?从意象与抽象来看中西绘画的和而不同》一文中指出,抽象思维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写意思维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不同的文化语言表达方式。如果说在西方抽象盛行的时代,中国艺术家受其影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方意象表达方式,那么其时的吴大羽、赵无极已达巅峰。用抽象来定义吴大羽、赵无极的画作本身是有失偏颇的,而在早已失去了“抽象”时代语境的今天,后人还用这种陈旧的语言方式去作画就好比我们临摹古人,既无新意,也无法超越,如果还要标榜“抽象”,那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绘画艺术发展到环球语境下的今天,秉承写意精神的中国水墨画早已摒弃了“山水、花鸟、人物”的古老分科程式局限,写意精神与表现主义殊途同归的意象表达成为中西绘画经历过激烈碰撞交融后返璞归真的本体回归。

齐白石:游鱼34×34cm
很多西化思想严重的画家总以为不搞点抽象,或者综合材料装置,自己的作品就不当代。另一方面,一些固守传统的画家只会关起门来临摹古人,开口闭口谈笔墨,在老纸老墨中较长短。我们应该警醒的是,这两种极端行为都不可取。艺术来源于生活,不写生的书画家是没有当下生活感受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不能本末倒置,材料不过是表达凭借,还应臣服于画者的当下情感。艺术家的生命状态大于艺术本身,所谓时代精神便在于材料背后鲜活感人的时代语境与生命体悟。
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现实是,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我们的艺术审美普及却一直在滞后与低俗混乱间徘徊。
艺术不是炫技,不是符号标榜下急于求成的装饰设计大师;艺术不是某位主持人写满恶俗的慌不择食,他们的吃相与网红大师卖力的痉挛嚎叫本质上并无二致;艺术不是抄袭西方穿西服装假洋鬼子,更不是东施效颦地穿长袍装古人。
那么,艺术是什么?环球语境下的中国水墨画将何去何从?

石鲁:春江水暖鸭先知
艺术是什么?
艺术家是天生的,不是教出来的。艺术首先是天赋,然后是自觉自悟,艺术属于那些懂得激活并驾驭自我天赋的人;艺术是性情的书写,是地域血液基因本来面貌与后天努力的自然合成;艺术是范宽式的雄强伟岸,是赵佶式的开宗立派形神并举,更是梁楷、法常式的笨拙质朴。彼时普罗大众眼里的“粗恶无古法”,现如今又有几人识?高山流水遇知音,好曲只给懂的人听就够了。艺术之高峰永远是少数精英群体的精神奢侈品,是曲高和寡的存在。
后晋赵莹主修的《旧唐书》有句:“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也可谓气格,这种首重人格修养的主张,也是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
复观书画之道,思想决定灵魂,灵魂决定艺术境界。如果说一个人的器识底蕴及艺术修养不够,那么其书画也好不到哪里去。反之,通过一个人的书画作品即可以看出其器识底蕴与艺术修养。如是,一个书画家的艺术修养决定了其艺途能走多远。画即是人,人即是画,二者不二。

高宏:异乡异语 水墨纸本 100x50cm 2018年
关良先生有句:“我一向反对做古人的奴隶,艺术上食古不化是没有出息的。一味模仿自然对象,艺术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见,在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画照片是没有出息的(参见拙文《画照片还有意义吗?冷军写实绘画拍出7千万天价,你怎么看?》)。今日之传统乃昨日之当代,今日之当代都在为将来有可能成为传统做准备。不合时宜的传统终将被时代所摒弃,当代便是为颠覆传统而来。传统不只局限于中国,古今中外前贤能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皆为传统。所谓传统与当代不过是为了表述需要借用的一个代名词以达到方便法门的呈现。
窃以为,艺术本无传统与当代之分,艺术所要呈现的时代精神一定是与时俱进同步吸收转化。凡我所见,皆为凭借,万物皆为我所用并不为所囿,饱含时代创见的同时并没有丢失自我根性基因底色方为众妙之门。艺术非独立自由不能孕育,只有那些能超脱体制的人才有可能与艺术有缘。艺术家是吃透传统,然后革传统命的人。艺术家是叛逆的颠覆者,懂得绕过前人的形式语言改弦易辙,另唱他曲。艺术家是疯魔的革命者,没有西方营养的水墨画是还在裹足的前朝女人,没有东方根性的水墨画是穿西服的假洋鬼子,唯两者皆而有之方可谓东西无碍的时代精神。

林风眠《仕女》
当曾经追随过现代主义的脚步并向艺术界扔进一个“小便池”的杜尚说:“绘画死了!”时,艺术本身并没有被杜尚抛弃,他所说的“绘画死了”是特指他所不齿的巴黎那些热衷于各种流派、主张的附庸风雅之流,他拒绝被既有的绘画风格束缚,包括自己采用过的技法在内。他抛弃的不过是彼时周遭让其生厌的绘画环境而选择了另一种不用画画的生活方式。反映在艺术上,他不与任何流派为伍,也不拘泥于绘画本身。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而形式总是千变万化。艺术的底线被打破,最核心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本身,把生活过成艺术的人成为了最牛逼的艺术家。艺术便是这样了,唯有举重若轻,方能驾轻就熟;“求美即不得美,不求美即美也”,艺术总是在认真里藏着不认真,正经里充满不正经。
作为一个中国人,水墨画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绘画传统,也是与这片文化土壤相匹配的最佳绘画表达方式,这种地缘优势就好比西方人写书法、画水墨比不上中国人一样。在此,区区并不是说中国画家不能画油画,恰恰相反,不同媒介材料的体验尝试必然会丰富画者的表达途径。区区只是想强调一下水墨语言对中国画家的重要性,这就好比一个最牛的中国语言翻译家一定要熟知汉语的重要性一样,他所懂的若干门外语,不过是深味自己本土语言的一种自然延伸。同理,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深受非洲文化影响,也吸收中国艺术营养,甚至还画水墨、画陶瓷,最终实现博采众长地转化成就自我,但他从未丢失自己西方本土绘画语言的主导地位。

吴冠中 小鸟天堂 68×137cm 90年代
水墨画就像西方的油画一样成为中西表达方式上天然的识别特征。作为两种和而不同的文脉传承方式,水墨画与西画彼此借鉴吸收、碰撞转化,并在精神高度上各有千秋,相逢互诉衷肠。
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中国人在水墨表达上也必须应时而变,水墨画的笔墨与线条变化之妙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当下情感服务,在表现形式上同样要有与时代相应的自我面貌方能体现其时代价值。
中国水墨画在经历了近现代中西交融的全球化启蒙后,在85新潮文艺复兴大环境的影响下,孕育出以朱新建为最高成就,李老十、朱振庚、石虎为重要代表的“新文人画”,他们给压抑良久的中国水墨画坛注入了一剂充满活力的猛药,美中不足在于他们浅尝辄止颇具玩味的绘画情调过于轻巧,还乏雄强恢弘之气。
如果说“新文人画”是中国水墨画长期桎梏后出现的一种很有时代意义的探索变奏,那么其后的“新工笔”不过是迎合当代艺术市场疯狂膨胀期的一次有效投机。上世纪80年代末由“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等艺术潮流开启的当代艺术热不过是彼时受西方潮流影响的一段稚嫩成长经历,人们长期压抑封闭的思想观念一旦得到充分解放后,这种艺术潮流也就光荣地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朱新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毋庸置疑,朱新建、李老十,朱振庚、石虎是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中国现代水墨探索最为突出的集大成者。他们进一步吸收古今中外绘画元素,在探索中国水墨从固守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道路上都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四人中,之所以朱新建成就最高,并非朱新建的笔墨功夫超过其他三人,而在于其笔墨语言的自我独立,在于画面背后的文化深度与真性情流露。其对传统水墨绘画内容和形式及道德文化的挑战,深刻反映了一位画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性解放现实的本体性思考。朱新建曾说:“中国画是文人画的业余游戏,文人画占主导地位。”此言豁然,彼时受西方冲击浅尝辄止的85美术新潮,他们情窦初开的幼稚模仿与朱新建的自我笃定对比鲜明。“画一无是处的画,绘中国式的性感”(参见拙文《【朱新建】画一无是处的画绘中国式的性感》),朱新建的时代意义在于他为我们重拾起“艺术只为完成自己”的新征程。
曾经在当代水墨界昙花一现的长安画派王炎林,台湾画家于彭都英年早逝,不免令人扼腕。活跃于当代水墨画坛的刘进安、李孝萱、李津是学院派佼佼者,老一辈的季酉辰,钟孺乾以及长安画派的邢庆仁,他们在创作盛年都曾力图由传统而靠近现代水墨且有过不俗的进取表现,然终究回归到亦步亦趋的抡瓢炒冷饭。而今,他们的锋芒逐渐式微甚至是倒退抑或学院痕迹固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成名过早或受体制束缚的外部环境影响,另一方面还在于其文化深度与内在思考不够。作为80后以当代水墨介入表达的优秀画家代表,我们兴奋地看到卞青在解构传统山水的同时巧妙地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之审美意趣,苦心经营精巧面貌是其深谙时风迎合时趣的成功之路,而这种直指观者的刻意设计目的性却又总是让人在兴奋之余如鲠在喉,可远观不可细嚼也。

朱振庚:选美图 纸本彩墨 136.3cm×69cm 2011年
中国水墨的未来
相较于当下单调沉闷的体制画坛,区区更倾向于关注那些超脱于体制内外把艺术玩得大胆有趣的画家。譬如老树的笔墨语言形式谈不上新意却诙谐入时,在丰子恺漫画图式基础上做了升级突破,画面形式更为灵动可人。他的题款及风格因为融入了活泼的当代语境思考而为大量年轻人所青睐。何建国在老一辈画家张光宇、祝大年、吴冠中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更为文人写意的形式美,遗憾之处在于这种缺乏文化深度且形式大于内容的文人画就此停滞不前同样会给人单一无趣之感。张进的笔墨语言有时或许流于荒率,但其泼辣大胆的探索状态是值得肯定的。李世南的大写意人物画颇具长安画派余脉锐意探索之灵光,确系长安画派继石鲁、王炎林后的在世高手,只是近年已渐露力不从心的颓势,若强弩之末,病气难调。而来自陕北的高宏,他的笔墨语言之所以更令我侧目,不仅在于其生猛孤傲的地域根性,还在于其质朴深刻的文人情怀。这种笔墨语言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长安之风是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西无碍,是谓厚重博大来日可期之欣喜。
我们再次回望充满变革与彷徨的近现代中国美术史,除了沿袭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前行的齐白石、黄宾虹等水墨艺术健将,还有林风眠、吴大羽、吴冠中等深受西法影响的画者在传统水墨绘画之外开了一扇窗。他们互为辉映,为丰富中国艺术的时代样式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齐白石、黄宾虹等在中国水墨艺术探索上都有革新意识,成为彼时中国水墨艺术之杰出代表,比如黄宾虹的积墨山水面貌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其时的西方印象派影响。尽管相较于宋元或者明清画坛典范之画格,他们还有距离,但其精神高度在当时也是风华绝代了。其后的朱新建、李老十等则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水墨画家之杰出代表,然其绘画语言总体还局限于中国文人画程式,其贡献与影响似乎还很难与齐白石、黄宾虹二君相提并论。

石虎:纸本水墨 20X20cm 2017年
再观吴大羽、常玉、赵无极诸君,则都是在画西画,虽然他们都是以西画媒介材料做东方表达的高手,但其西画媒介属性与相关语言形式又决定了他们在大师林立的西方艺术界要获得一点成就与认可是何其不易(铩羽而归的徐悲鸿、陈丹青便是代表)。作为中国人画油画,即便他们已经做到了极致也休想去提与西方大师一较高下,这是源于根性的文化土壤优势有别使然。与吴大羽交集甚深的林风眠,吴冠中虽然是以水墨绘画为特色,但林风眠吸收西画形式的水墨表达还只是简单挪用,吴冠中的江南文人绘画又过于强调形式美,以至于学生辈无一有逸出者。可见,我们在看到他们竭尽光辉灿烂的同时还应察觉,他们因时代所囿,以西方样式为主体的中国绘画改革之路是一条死胡同,此路今日难以为继的凄凉尴尬便是明证。
如此看来,中国水墨由外而内的变革已经穷途末路,中国水墨的未来在于由内而外地生发变革。也就是说中国水墨必须坚持以艺术之根性——中国文化主体来吸收西方营养开枝散叶,才能真正突出中国画艺术的根性基因及识别特征,而延续千余年的水墨画无疑成为了中国画艺术最高成就之代表。这就好比杂交水稻的研发需要依循不改变水稻本体属性,可供食用营养为基础的优良增产改善方为成功之道。
应该说,趋于程式守旧的中国传统文人画自金农之后就已逐渐走向没落。中国近现代科学、文明、经济的普遍落后其实质是闭关锁国的大环境所带来的思想的落后。这种思想落后必然也会影响到中国水墨艺术观念的守旧与落后,继而造成近现代100余年里世界艺术的中心只在发达繁荣的欧洲与美洲之间传球,中国画俨然成为没有话语权的落伍者。正如蔡国强一语:“东方100多年来没有好画家,东方绘画放在毕加索或者西方大画家的旁边,显得很乖,很呆板。”近现代虽然有20世纪初最早走出国门的那一批留法画家的努力,然又经过抗日、国共战争、文革等波折,直到改革开放后艺术界“85新潮”的到来,中国艺术才逐渐走上亦步亦趋地稚嫩模仿成长期轨道。毋庸置疑,这种受西方思想启蒙的模仿与反思乃至探索阶段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必要与必经之路,更是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并进行自我革新之前提。绘画语言的革新是艺术活力生生不息并得以前行的首要前提,尽管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应当首肯这批中国近现代画家的探索精神与积极贡献。正是因为他们的探索与尝试才得以让后人去反思少走弯路,并肯定未来之方向。

李世南:《绿了芭蕉红了樱桃》-7 35cmX46cm 2016年
在艺术市场逐渐回归理性的今天,在中国经济近百年来空前繁荣,经过思想启蒙后的文化精英界已逐渐融入国际并自信于西方的今天,东西方艺术也逐渐回归本体,各回各家。大国自信在今春抗疫反转中可谓有目共睹,我们从最严重的世界核心疫区成为最有经验成效的抗疫典范并还能帮助到意大利、伊朗等很多国家,这次抗疫也让全球再一次瞩目中药的神奇。今春短短几十天的疫情反转与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的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窃以为,中国水墨是潜沉于中国文化里的东方思维,近100余年来,中国水墨相比于西画就好比中药之于西药之尴尬,好比中国文化水性的柔软与直觉诗意之于西方文化逻辑思维的微观具体。表面上看,二者地位悬殊,但内在的能量与改变正在潜移默化地渗透,这种变化就像太极一样阴阳和合,对立统一。恰如硬币之两面,中国近100余年来水墨画在世界舞台的失语只是短暂的滞后,代表东方思维的中国水墨一旦被充分激活,其潜力必将璀璨惊人。在不久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水墨与西画平起平坐是势不可挡的天道轮回,甚至还会像今天的疫情处理危机处理上出现“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足为怪。
综上所述,中国水墨画迎来了新一轮的沉寂与洗牌,也必将迎来新一轮披荆斩棘屹立于时代潮流的独立艺术革命者。甚至可以说,中国水墨语言作为中国经济全面崛起之大变革时代的见证者与承载者,它遇上了东方艺术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前所未有的契机。
江山代有才人出,时势还将造英雄。人类的个性生命体验不会消亡,书画作为表达生命状态的一种语言便不会消亡。西画不会消亡,水墨画同样不会消亡,绘画这个游戏会因为今天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语境影响而与时俱进,常变常新。
八大山人在《鱼鸟图卷》的题跋有云:“文字亦以无惧为胜,矧画事。故予画亦曰‘涉事’。”无惧为胜,这种波澜不惊的平常心作画观便是我们延绵不息的文脉,它是中国水墨画得以再次崛起的契机与未来。

张进:花下酒透瓶香
艺术家是在思考与本能之间赤足狂奔的人。艺术家首先是思想家,是器识宏大的文化底蕴深厚者,只有树立起本体性独立思考的自然宇宙观方为艺术灵魂之所在。作为传统的捍卫者与创新者,黄宾虹说得好:“画有民族性,而无时代性;虽有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这个不移的精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代表东方思维的中国水墨精神,是人性与人类文明亘古不变且殊途同归的精神高度本质追求。
优秀的批评家与收藏家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家,是能看见并创造未来的人。笔墨当随时代,其实质是思想与观念当随时代,如何让中国水墨在与时俱进中“老树发新枝”,这是每一位有情怀的当代中国艺术家都要面对的课题与责任。
如是,我们需要立足当下往前看:
崛起的中国水墨必将在世界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那个下笔见性,不负于时代的艺术家已在路上,就看阁下有没有超前的鉴赏眼力。
2020/3/28
后记:
此篇在本人拙文《环球语境下中国水墨画的契机与未来》(详见《中国书画》2020年第2期)以及《中国画家,改工作了吧》基础上修稿而成,修修补补越写越长,对艺术之未来之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肯定,这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艺术是曲高和寡的精神饕餮,很多时候是无法言说,也无需言说的,余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做点文字记录,更多是为完成自己。就像这长夜尽头的黎明,总是让人兴奋又期待,不禁让人想起诗人顾城一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苏轼魂归处为什么是河南?
相关新闻
大开大合 水墨淋漓 水墨山水画家:王本杰
自然中的山水,是一种精神。是造物者创造之初,所赋予自然生命的灵性。绘画中的山水,又有一种精神,是画家情感的家园,王本杰老师的画,在写意性和写生性的基础上,将笔墨进一步概括
金鼠献瑞:画家王佰如喜迎中国年
深厚的笔墨功力,娴熟的笔墨技巧以及坚实的造型能力促使王佰如深入都市、深入生活,将作品立意定位于城市山水,以及采用新的创作手段改变自己,改变思维模式,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取得了可喜成绩。
水墨重彩画家武星宽先生的艺术特色
来自于蒙古草原的中国画艺术家武星宽先生,因其各种偶然而又必然的生活遭际,而获得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在传统水墨艺术的诸多边缘地带获得了创新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墨重彩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