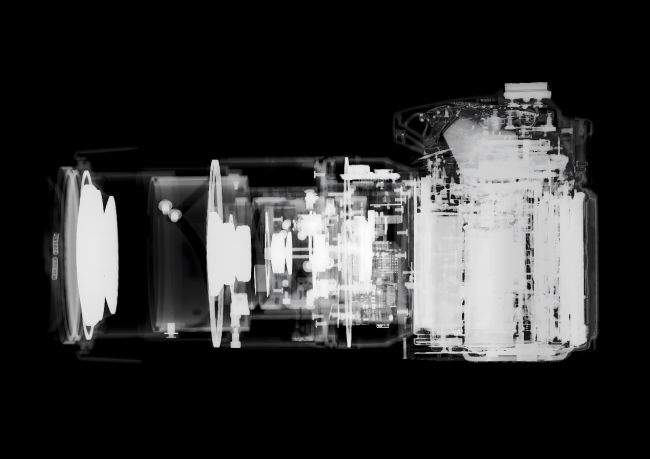沙漠、丝绸之路与美食的全球化
![《沙漠与餐桌》,[美]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版。](https://img1.utuku.imgcdc.com/650x0/culture/20211123/8d4f35d3-e66b-4b78-9f0b-62adf9c1e020.png)
《沙漠与餐桌》,[美]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版。
15世纪,欧洲人的餐桌上有什么?
随着15世纪东亚香料的价格在西欧一路飞涨,为寻求黑胡椒和肉豆蔻而踏上旅程的富有进取精神的欧洲航海家驶向了未知的水域。受到葡萄牙国王“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的委托,瓦斯科·达·伽马与兄弟保罗在1497年率领由4艘船组成的舰队启航,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最终到达卡利卡特。达·伽马的航行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旅程一样,彻底改变了全球交流的本质。关于地理大发现之文化影响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亚洲的食材和香料引进到新世界之前,欧洲人的餐桌究竟是什么样的?
意大利美食似乎是欧洲特色饮食的集大成者,然而,意大利饮食的许多核心食材直到近代才传入地中海地区。番茄在大约3000年前的南美洲被驯化,后来被西班牙探险家当作稀罕物带到欧洲,又经过好几个世纪才成为受大众欢迎的食物。意大利面以及在砖砌烤炉中烤制的比萨饼底,可能都是由中世纪的商人从阿拉伯世界带入意大利的。将亚洲大部分地区用烤炉或馕坑烤出的薄面饼稍做改动,涂上黄油、香草和酱料,便成了比萨饼底。只需再加一些碾碎的番茄,意大利人便创造出了本国的代表菜品。与比萨类似,面条也是在约1000年前跟随阿拉伯商人传入地中海地区的,它很可能起源于东亚。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人接触到面条之后,很快便将其纳入自己的特色饮食中,后来也在面条上点缀碾碎的番茄。
另一种意大利主食波伦塔只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欧洲普遍食用的谷物粥略加改动而已。不过,今天的波伦塔基本都以玉米为主要原料,而玉米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农作物。意大利团子(gnocchi)则对我们熟悉的饺子进行了有趣的改造。今天,意大利团子基本都用马铃薯——也就是土豆——烹制而成,而马铃薯是在安第斯山脉高处被驯化的根茎类作物。就连意大利美食中用来调味的红辣椒和提拉米苏中的巧克力也是从新世界引进的物种,辣椒早在约6000年前便在墨西哥被人类驯化,而巧克力则发源于公元前二千纪便存在于中美洲的一种不加糖的饮料。
有些意大利人或许难以接受这一理念:他们的大多数特色饮食都是在殖民时代而不是古罗马的宴席上发展而成的。不仅如此,另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现代意大利的酿酒葡萄并非出自有数百年历史的意大利葡萄藤,而是生长在从北美进口的砧木上。19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葡萄大瘟疫”摧毁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葡萄园,法国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这场葡萄病害的始作俑者可能是葡萄根瘤蚜,这种蚜虫(很可能是学名Daktulosphaira vitifoliae的品种)摧毁了葡萄藤的根系。欧洲葡萄酒产业在20年里几乎完全停滞,直到两位法国植物学家发现,将藤蔓嫁接到完全不同的北美葡萄品种砧木上(最初选用的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夏葡萄的根)能够提高植物对病害的免疫力。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葡萄园逐渐开始栽种嫁接到北美抗病砧木上的葡萄藤,慢慢恢复了生机;这样说来,欧洲出产的所有葡萄酒都应该感谢得州葡萄。

1865年到1872年的锡尔河一带,双峰驼商队载着商品前往市场,摄影师不详,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片与摄影部,出版社供图。
丝绸之路对各国美食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很多地方特色饮食中,外来食物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沙俄帝国为中亚带来了许多新式菜肴,比如蔬菜汤和罗宋汤,还有俄罗斯馅饼和薄煎饼。就连当今许多中亚菜肴的主要食材——稻米——在当地扎根的历史也不过区区1500年或者更短。
《沙漠与餐桌》关注的重点是全球化如何影响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文化的发展,以及今天全球化如何持续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尼科洛、马费奥和马可·波罗的远行,以及数以千计名不见经传的祆教祭司、粟特人、波斯人、回鹘人、古吉拉特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旅程,都对当代人的食物清单产生了影响。当这些旅人途径亚历山大港、巴格达、贝鲁特、布哈拉、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卡菲尔卡拉、麦加、马斯喀特、片吉肯特、泉州、撒马尔罕、塞萨洛尼基、吐鲁番、乌兰巴托和西安等城市时,他们一路捡拾起各种从未见过的植物和不同品种的农作物,最终将它们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位作家曾写道:“将我们称为食用植物的仆人并不算夸大其词,人类勤勤恳恳地将它们送往世界各地,像奴隶一样在精心打理的果园和田地里照料它们。将这些人类活动称为种子的传播,这完全不是夸大其词。”
赶着大篷车的商队和香料商贩走遍四海,他们通常会说多种语言,具备久经磨炼的社交技巧;他们善于开发新市场,将生意拓展到全球各地,而且擅长结交新的盟友。他们驾驶的大篷车不仅穿越了沙漠,还跨越了政治的壁垒。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携带各种传奇植物的祖先一路同行,这些植物最终演化成了无可比拟的大马士革杏、大名鼎鼎的哈密瓜和撒马尔罕的金桃。史前中亚人还曾在阿拉木图种植适合做蜜饯的小苹果,在阿什哈巴德和撒马尔罕栽种硕大多汁的甜瓜,在吐鲁番培植外皮呈鲜黄色、能酿出甘美红酒和制成深紫色葡萄干的葡萄品种。
如今,东亚厨房的烹饪魔法也是数千年来各种异域食材——尤其是香料——通过贸易输入当地的结果。吴芳思创作了数本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她是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的负责人。她指出:“除了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奢侈品,食品便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因为它们大大拓展了中国特色饮食的潜力。”她还说:“可能让很多中国厨师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某些基本原料最初都是进口产品。芝麻、豌豆、洋葱、芫荽以及黄瓜都是在汉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丝绸之路为世界各地的厨房带来了新颖的食材,但它对人类历史和农业还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在各种农作物通过内亚进行早期迁移的过程中,随之一同传播的意义重大的创新之一便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伊斯兰古代村落发现的古代植物遗存年代在8世纪至13世纪,一位植物考古学家基于这些遗存指出,当时的农民已采用复杂的轮作制度。冬季作物包括二棱和六棱皮大麦、易脱粒小麦和有颖壳的小麦、黑麦、兵豆、豌豆、鹰嘴豆和蚕豆。夏季作物则有棉花、水稻、芝麻、黍和粟。这位学者还鉴定出一些果树和葡萄植株,以及少量蔬菜和香草。
历史文献表明,在俄罗斯扩张之前,中亚已确立了复杂的农作物轮作制度。在1821年和1822年,探险家詹姆斯·弗雷泽在经由费尔干纳重走丝绸之路时便注意到当地实行轮作制,而且指出这种轮作制与泽拉夫尚地区的耕作方式十分相似。他记录了冬季作物和夏季作物相互替代,同时与果园和棉花田混合的情况。他还指出,在海拔更高的地带,水果多种植在山麓丘陵,同样的种植情况还有杏树、胡桃树和开心果树。1873年,尤金·斯凯勒在穿越费尔干纳和泽拉夫尚时,记载了当地冬小麦、大麦和玉米三年轮作、一年休耕,夏季种植水稻、高粱、棉花、亚麻和各类蔬菜的做法。

丝绸之路上的额弗剌昔牙卜古城遗址远眺的景象,这座古城坐落在贸易路线的核心地带,在公园一千纪中期便存在,后于1220年被蒙古骑兵摧毁,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摄影,出版社供图。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冬天是农户休养生息的时期,因为农作物不生长。这为进行手工艺品生产和发展社会纽带等活动留出了时间。但是,经济和人口压力逐渐导致冬季和夏季作物轮流播种,从而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此外,灌溉工程的建设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但也需要大量额外的人力。
向干旱地区引入耐旱、生长迅速的夏季作物同样引发了类似的进程。小麦向东亚的传播、黍向西亚和欧洲的传播,加之集中灌溉项目的建设,这些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正如内奥米·米勒及其同事所指出的,随着大约2500年前灌溉系统的发展逐渐成熟,黍在西亚的重要性也日渐提高。有了灌溉,已经完成冬小麦收获的田地里便可以种植粟米。同样,这种轮作制度也对土壤和农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与之类似,小麦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传入中国,随着汉代官府管理的大型水坝和灌溉项目建设而成为主要的冬季作物。同样在汉代,有犁壁的犁投入使用,铸铁犁铧首次实现大规模生产。历史学家认为,中国早在汉代以前便已有犁的存在,而且有可能是从西南亚经过中亚传入的。自汉代之后,小麦便与夏季水稻搭配实行轮作。复种轮作的增加以及从中亚传入的磨粉新技术可能是唐代小麦的普及程度提高的原因,尤其它可制作饺子、油饼和面条。生活在唐代城市的中亚人烤制的烧饼就像缩小版的馕(中亚地区至今还在烤制这种叫作馕的薄面饼)。发酵乳制品在这一时期也越来越流行。
北宋(960—1126)灭亡时,集约型农业在中国达到了顶峰,南迁的难民将种植小麦的经验也带到了南方。此外,南宋(1127—1279)仅根据秋天的收成收取赋税或地租;换言之,农民在春季或初夏的收成无须缴纳赋税。生长迅速的水稻品种传播至南方,使偏远的南方一年可以种植两轮水稻。在中国西部的某些地区,大麦成了与荞麦搭配轮作的冬季作物。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第一代实行轮作的农民或许从中获利颇丰,但轮作的长期影响是:粮食富余而导致人口增加;粮食的价值下降(农民需要扩大收获才能养家糊口);土壤肥力迅速耗尽。由此可见,农作物轮作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和粮食的过剩,最终使农民的负担更加繁重,生活更受压迫,环境也日益恶化。
与此同时,更加丰富的食物让一部分人口从田间劳动中解放出来。空闲时间的增加让人们得以专注于手工业生产或教育研究,从而使亚洲和欧洲都迎来了艺术与创新的黄金时代。过剩的粮食往往也会投入军队建设之中,这是整个旧世界实现农业密集化的结果。军事化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冲突范围,因为维持庞大常备军的国家不可能不使用这支军队。就连强大国度的军事力量也体现了以中亚为跳板的早期植物交流模式:罗马军队以未发酵的粟米面包和粟米稀饭为食,可汗麾下的蒙古铁骑则以小麦面粉制成的饺子为食。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系列地理线路的集合,
也是欧亚大陆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发展过程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对东亚、南亚和地中海的帝国及商业中心产生的影响展开。然而,随着中亚地区科学考察活动的增加,如今学者们对丝绸之路本身的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随着新考古方法的应用和多学科联合发掘的开展,将中亚先民视为古代世界边缘群体的老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淘汰。过去人们认为草原游牧民族都是悍勇的战士,在庆典上用敌人头骨制成的酒杯豪饮(参见希罗多德的记载),这种印象现已被更加深入细腻的认知所取代。斯基泰文化、塞卡文化、乌孙文化和匈奴文化由一系列奉行混合经济策略的人群融合而成,他们既放牧绵羊也放牧山羊,搭配种植好几种不同的农作物。史书中斯基泰骑手穿越绵延数千公里的空旷草原的形象逐渐被取代,人们意识到,这些先民形成了由小型游牧家庭构成的广泛的社会网。
数千年来,这些长满绿草的缓坡是骆驼商队和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的食物来源;冰川融水汇成的河川流过水田和果园,中亚的野生林地出产各种水果、坚果和野味。进入20世纪后,这些树林在经济中仍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勒泰至帕米尔一带。在中亚南部以及泽拉夫尚和费尔干纳的河谷中,生长缓慢的灌木林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草原植被取代,尽管如此,植物考古学资料以及曾经生长在树林中的树木的驯化形态依然能够体现这些灌木林的重要性,例如开心果树、杏树、沙枣树、山楂树和樱桃树等。在6000年的历史中,人类一直在影响该地区的树木品种和森林植被的构成。餐桌上的苹果派和酥皮黄桃派不仅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结晶,也凝聚着整个内亚人类定居的历史。

一位商贩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郊外的市场上兜售商品,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摄影,出版社供图。
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古典学者、汉学家和考古学家仍然支持丝绸之路发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观点,但考古数据显示,丝绸之路沿线的互易和互动似乎在此之前很久——公元前三千纪末——便已初现端倪。早期的交流模式看起来更像是自然的扩散而不是有组织的互动,但那仍然是丝绸之路贸易文化现象的一部分。理解中亚如何形成有组织的交流路线的关键在于从公元前四千纪开始专为向萨拉子目等高海拔矿业城镇供应货物的路线和方法。在公元前一千纪结束时,在政府靠税收建立的军事要塞的保护下,贸易商已经拥有相对成熟的、在中亚各地运送货物的线路。
公元前一千纪,整个内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结果是形成了尼科莱·克拉丁(Nikolay Kradin)口中的“复杂的牧业社会”,同时也导致了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正如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所指出的,人口的增长和社会复杂性的提高通常与农业新技术的开发或引进以及互易交流的加强紧密相关。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将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系列地理线路的集合,还可以将其视为整个欧亚大陆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推动了整个旧世界的变革和社会复杂性的日益提高。丝绸之路成了食物全球化重要的渠道之一,这条互易交流的走廊在过去5000年里一直在影响和塑造欧亚大陆各地的文化。
最后,我将以欧文·拉铁摩尔的话作为全文的结尾,在内燃机尚未发明、二战尚未彻底颠覆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20世纪20年代初,这位传奇探险家和学者曾随骆驼商队一起沿丝绸之路而行。在1929年写下的文字里,拉铁摩尔对他在中国西部多地观察到的变化扼腕叹息:
在我们的时代,蒙古和中国新疆一带的商队向外输出的每一批货物都有所不同,但商旅们始终采用亘古不变的古老运输方式,仿佛白人从未在亚洲出现过一样。然而,他们的末日已然降临。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在中国,时间的流逝往往以半个世纪为单位),在这样的时代,懂得师夷长技的人将修建起连通宁夏和兰州的铁路,沙漠商队很快便会沦为在阿拉善的沙海与大草原之间飘荡的贩夫走卒。走进这些市场的感觉十分奇怪——感受到难以名状的、走遍天涯海角的沙漠商队昔日生活的脉动,同时意识到明日的阴影将让他们的一切传统和特色面目全非。在卸下小小的行囊之后,赶骆驼的人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城市,似乎期望在半小时之内慢悠悠地走回家中;然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直走到营地,大篷车组成的商队正在山丘背后等待着他,骆驼正在吃草,等待再一次装满行囊。等到营地拆除,他将再次艰难跋涉,一路抵达中亚。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只要离开家乡、搭起帐篷,他们便能不慌不忙地远离充斥着电报和报纸、刺刀和戒严的文明社会,走进一片神秘而辽远、只有他们知道入口的土地。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相关新闻
构建敦煌文化制高点 打造丝路旅游枢纽站
新中国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地处陆上丝绸之路黄金段和“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的甘肃,再度迎来黄金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