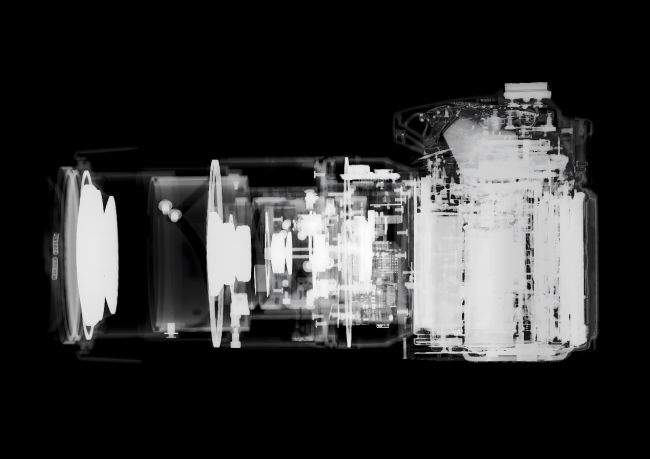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中国与世界社会》看世界中的中国(3)
费正清学派的视野是辽阔的,但在我看来却仍有拓宽的余地。这些美国学者中,有些人是从政治和军事层面去梳理中国的对外关系,还有些人是从经济学角度将清帝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作为研究课题,而第三类学者则把目光集中于文化影响和文化输入问题,并将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作为重点。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曾就一个专项课题做过研究,这就是1930年代英国资本在华扮演的角色。当时,中国一度涌现出一股利用外资的潮流,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
当我在1980年代写作本书时,我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更开阔的框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一并纳入进来。因为在我看来,把这些视角区分得过于清楚,是一种人为和刻意的做法。同时,我还为本书增添了另一个视角:当时我正在为筹备中的另一部作品搜集资料,其主题是18世纪(即启蒙时期)欧洲学者对亚洲的看法。这本名为《亚洲的去魔化》的作品于1998年出版,其中文版也已于不久前问世。于是,我就把自己对欧洲对华认知这一问题的兴趣作为引子,写下了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开篇的这一章讲述了欧洲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种种印象,这些印象中当然不乏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基于理性观察得出的,其中有些已经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得到了确认。将这一话题也纳入本书的视野,于我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选择了“世界社会”这个关键词作为本书的书名,这个词后来成为“系统理论”(Systemtheorie)当中的重要概念。不过,在这套理论中,“世界社会”有着另外的含义,因此我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本书中的“世界社会”指的是什么。在这里,它的含义并不是说,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某种全球统一的社会结构,这种情况迄今仍未发生;其所指也不是哲学家的乌托邦式幻想,即未来某一天人类将迎来一个全球一统的世界社会,到那时,民族国家也将不再发挥作用。康有为在1900年后不久发表的《大同书》中,便曾表达过这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