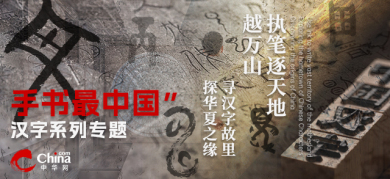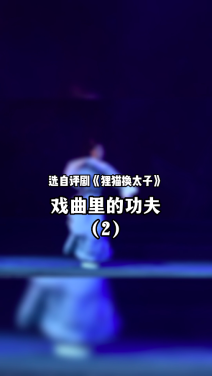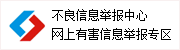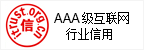金庸百年诞辰纪念 ——金庸笔下的疯女人

陈好版阿紫

米露版梅超风

康敏版马夫人

李若彤版王语嫣

翁美玲版黄蓉

刘亦菲版王语嫣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疯女人不再符号化
为此我还真的迅速把多年阅读金庸的经验拿出来翻检了一番。确实,相比起传统武侠作家,毫无疑问,金庸属于新派,属于现代,属于“五四”之子。他的小说技巧完全不同于明清乃至民国大批艳情小说家的范式,而是大量采用了“五四”之后现代小说的新的笔调,甚至有直接照搬当时翻译小说的段落(有不少人考证过金庸小说与大仲马小说的关系,比如《射雕英雄传》里某些段落完全照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续集)。
因此,在他的小说里,给一些所谓的坏女人的角色,加上来龙去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梅超风并非天性嗜杀,而是在恋爱失败,被师父逐出师门后逐渐疯狂;叶二娘也不是天生恶人,要不是与僧侣情人的爱情不容于世,加上婴儿被坏人掠走,她不会一步步走向疯狂的道路,甚至变态到以杀戮婴儿为游戏。金庸大概吸取了当年刚进入中国的心理学的一些观点,给叶二娘的人物设定中,她的杀婴来自于之前自己的婴儿被人夺走的过程,与其说是因果循环,不如说是心理归因。
这些描写都让金庸小说里的恶女不再符号化,而是有一定厚度,也给后期改编金庸原著的影视剧导演提供了灵感。不少《射雕英雄传》的改编中,甚至会添加梅超风与恩师黄药师的恋爱情节,大概还是原著里的梅超风恶的来历,有魅力,有足够的模糊性,改编者普遍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人物上做点文章。
可是这点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的代表金庸足够新锐,已经有了女性主义的思考,所以给自己小说里的妇女群像很多斑斓色彩?仔细一想,完全不是这样,金庸的现代性止步于“五四”思潮,就像他的亲戚徐志摩一样。他们这代人受“五四”运动影响颇多,能够让传统小说的纸片主人公变得立体,让女性不再单薄。但与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家相比,还是距离甚远。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他小说中对疯女性的描摹,颇为有趣——足以表明作为男性作家的金庸对拒绝遵守传统规范的女性的态度与看法。
当然我们不要求金庸是具备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家。时代限制,个人性格,包括个人经历都会让每个作家形成自己独到的对女性的看法,是与不是女性主义作家并不重要。值得讨论的是,金庸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疯女人”角色,恰恰与女性主义热衷讨论的西方经典小说中的“疯女人”形成对应关系。
若干经典的疯癫女性
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梅超风、叶二娘,金庸小说里还有若干经典的疯癫女性——比较典型而有趣的是《天龙八部》中的阿紫和马夫人。金庸能够把阿紫写得活色生香,不那么可恨,还是依靠自己的经典本事,用爱困住这个女人。为情所困的疯癫女性,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缺失的一笔,但在现实中又普遍可见。阿紫的嗔怒、邪恶,包括带点虐恋性质的男女关系,都只有一个理由:她为情所困,爱上了大英雄乔峰而不得,所以逐步走向崩溃。这是一个经典的古典小说悲剧女主角的形象。
为了这个原因而疯癫的阿紫显得凄婉动人,包括最后的挖眼,从悬崖跳下去的死亡模式,使得阿紫的形象惨烈而生动,尤其是阿紫的外貌还那么明艳——这个角色让我们想到歌剧《托斯卡》的女主角托斯卡,想到《呼啸山庄》里的卡瑟琳·欧肖,属于其来有自的悲剧女主角。
小说里另一个经典的女配角马夫人,其实同样是为情所困。征服欲极强的马夫人一直属于情路上的强者,基本上没有输过,但乔峰对她的冷漠,让她的整个心理发生了极度的变态反应,开始成为折磨乔峰的背后团伙里的带头女人。直到乔峰变成萧峰,恢复了契丹人的身份,被整个武林所排斥,她还不满意,邪恶溢于言表。在秘密暴露后,马夫人被阿紫折磨而死——死状极惨,堪称金庸小说中死亡的经典:浑身小刀口,还被涂满了蜜糖,爬满了蚂蚁,几乎属于虐杀。与其说这是阿紫将之折磨而死,不如说金庸是借助阿紫之手,对自己厌恶的疯狂女性予以惩戒。
金庸无疑讨厌这个马夫人,一个妖娆美丽、征服欲很强的蛇蝎型妇女。他给她安排的复仇理由其实不太成立(现实中几乎没有女性的变态心理来得如此牵强)。所以这个人物其实也并不成立,但却因为过度突显的变态,而让人记忆深刻。我们只能将之解释为,金庸在现实中,对此类型的女性恐惧而厌恶,所以特意安排了她奇特的一生。
金庸对疯女人有理解也有偏见
金庸小说里的疯狂女性,以马夫人、梅超风、叶二娘为代表。这几人的死亡都极为疯狂,都是作者代表社会给予她们的惩罚,无一善终。这大概也符合集体的想象:疯女人不会有好的结局。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尽管金庸对她们有同情,有理解,但还是不肯给她们以美好结局。在漫长的时代里,在社会的集体想象中,疯女人怎么可能有好的结果?离群索居已经是上帝给她们的最好安排。金庸安排她们的惨死,也是一种给她们的救赎,让她们早日解脱——典型形象还有在烈火中焚烧自己而死的李莫愁。这画面简直是恐怖而凄美,让人想起了《秦俑》里面的那首歌曲《焚心似火》。
不变的模式是,李莫愁也是因为男性的抛弃而陷入了疯狂,成为了美丽的疯女人。这和西方文学经典里塑造的疯女人别无二致,《阁楼上的疯女人》很多也死于火焰,或者离群索居一辈子。这一点上,金庸和他的西方同行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代表上帝,惩罚了她们。
疯女人大概只能改邪归正,才能得到所谓的幸福生活。在《射雕英雄传》里出现的瑛姑本来已疯,但是在《神雕侠侣》中得到了男性的爱情,因而和周伯通白头偕老,隐居在桃花深处。这种臆想中的美好结局,是金庸给他的符合社会伦理的女主角的一个甜品。
金庸更像传统社会里的道德男性
再说一遍,不是要指责金庸,而是相比起真正伟大的作家,金庸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写过一本文学评论的小册子,名为《萨德式女人》,认真分析了十八世纪色情作家萨德的寓言式小说《朱斯蒂娜》中两姐妹的命运:贞洁、虔诚的女主人公受尽了磨难,被男性侮辱,强暴,折磨;相反,女主人公邪恶的姐姐,一路上折磨男性,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一直拿身体和男性做着各种交易,却一帆风顺,最后甚至做起了主教的情妇,成为社会上标准的成功者。萨德的小说只能作为寓言来观看,但安吉拉·卡特将之称为“道德色情文学作家”,显然看到了他小说里足够的力量感。作为欲望客体的邪恶女性未必需要受到惩戒,反而可以逍遥法外,“成为欲望的对象就要被定义为被动。在被动中生存就要在被动中死去。这就是童话故事中完美女性的寓意。”——卡特认为萨德开创性地不把女性视作单纯的生育工具来书写,“他看到了女性在生理特征之外的存在,因而在此意义上解放了女性。”譬如在萨德的小说中,坏事干尽的姐姐茱莉爱特最终并没有受到惩罚。
金庸特别像传统社会里的道德男性,认定疯女人不得善终,她们肯定不会有完美的未来。他有时候简直像大家庭里的族长,一直在小说里惩戒那些贪婪、不受规矩、放浪形骸的女性:李莫愁活出了真我,但在火焰中焚烧了自己。相反,围绕着男性默默奉献、表现良好的女性,则会收到金庸颁发的奖牌——比较典型的如《倚天屠龙记》里的围绕张无忌转悠的几个女性。他自己在后记中承认,最爱的是默默奉献、美丽而深藏不露的小昭,甚至因为不能把她安排给张无忌,而有点惆怅。
小昭几乎是金庸小说里少见的完美女性:美丽、善良、温柔、乖巧,对待爱人多情,也丝毫不嫉妒,最终的分别虽然带了一点哀怨,但纯然是她自己选择的牺牲。谁不爱这样的女性?相比之下,刁蛮的赵敏,复杂的周芷若都显得不那么可爱了——大概金庸也知道这样的女主角近乎捏造,所以只能让她远走波斯。类似的完美女性,还有《鹿鼎记》里的双儿,也是无私奉献。巧合的是,在香港导演的金庸电影改编中,这两个角色,都由以美艳著称的邱淑贞扮演,有意无意中帮银幕下的男性观众圆梦。
疯女人们只是金庸的配菜
同时代作家高阳的女性描写,显然要比金庸复杂而写实。高阳以历史小说写作而著称,包括他几乎按照自己的思考,重新写了曹雪芹的家族故事——里面的女性群像丰富而多元,有侠女,有荡妇,有贵族家庭的太太、小姐,也有混迹江湖的底层弱女。高阳显然对惯于风月但又有一身侠骨的中年女性充满了爱慕,他的不少小说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女性角色;拯救陷于险途的男性主人公的,往往是风尘中的女性,她们显然没有按照世俗规范去要求自己。而高阳也没有陷落于封建笔法,给她们安排一个归宿。有的烈女子,甚至以自杀为反抗险恶社会的方式。对比金庸所描绘的疯女人,高阳的女主人公简直光彩照人。
疯女人们只是金庸的配菜,几乎没有一个疯女人能够获得主角的笔墨。金庸显然更偏爱他的那些颜值爆表、武功高强的女主人公们——她们或机智,或纯洁,或痴情。可惜这些女主人公都像童话里的人物,无论黄蓉还是小龙女,都好像丧失了血肉之躯,只能存在于“成人的童话”里。一旦进入世俗的世界,这些仙女们也就不那么可爱了。最典型的是《神雕侠侣》中的成年黄蓉,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宝玉的形容:女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出了嫁,慢慢竟变成鱼眼睛了。
大概金庸还是愿意他的小公主们生活在童话里。这让人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江湖传说,他在现实中追求过的大美人夏梦是他许多经典女主人公的原型——那简直不是凡尘中人。而一旦弃他而去,之后的故事,金庸再也不愿书写。
(标题取自陈墨先生《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谨致谢忱。)
问答之创作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梦》,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到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说有自己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摘自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推荐阅读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电影,不仅是一部艺术品,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推广的有力载体。今年,暑期档的中国电影用多种类型题材向优秀传统文化致敬,用光影传承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也展现着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太原古称晋阳,有5000年文明史、2500多年建城史,全市现有2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古遗址334处、古墓葬121处、古建筑932处、石窟寺及石刻48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96处。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民以食为天”,自原始农业诞生之际,我国的农作物体系就展示出“多元交汇、多元一体”的特点。有些新物种不仅在华夏大地上“站稳了脚跟”,还能“反客为主”,成为今天散落各地的地理标志产品。一起来看历史上那些关于“老祖宗严选”的趣事。
四川大学博物馆 荟萃西南地区人文自然珍宝
“四川大学博物馆注重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从学者视角和学科维度精选展品,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构建可看、可听、可闻、可触的综合性展陈体系,力求增强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兴趣。”
微综艺碰撞出“治愈”火花
网络微综艺《我爱我很棒旅行日记》日前收官。作为今夏最与众不同的一档多人旅行Vlog,该节目以“旅行日记”的形式聚焦余秀华、完颜慧德、苏敏、邓静四位有不同故事和经历的女性嘉宾,凭借真实治愈的“碰撞”受到大家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