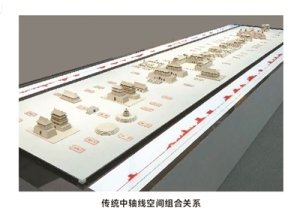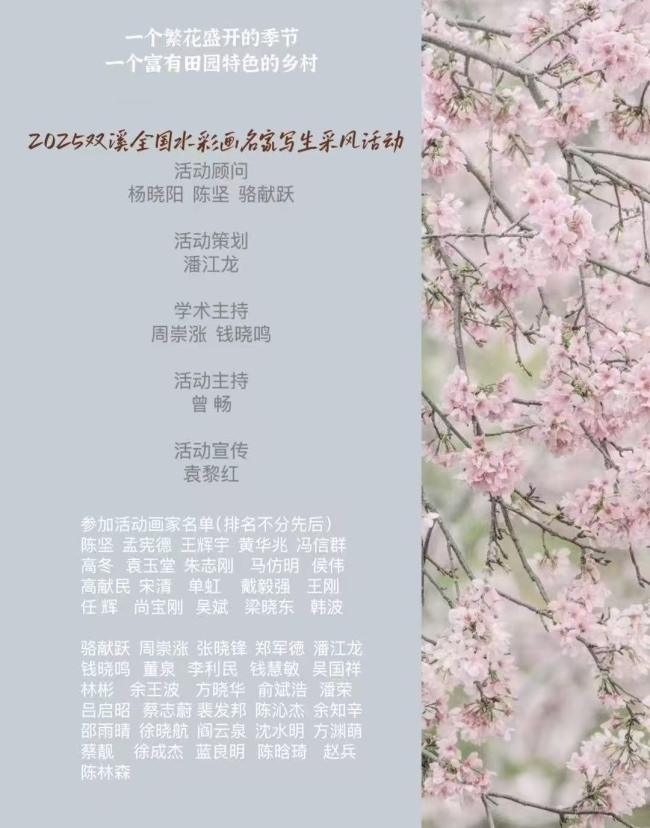邵光亭:书法艺术的现代性问题(4)
传统文人有两种特质:一是学识胸怀,二是风骨情操。既不崇敬学问,也不敬畏古人,顽固傲气,从心所欲,不知自警自惕。我看到一些鼓吹现代书法的先生后生们,连书法创作最基础的文字关都不及格,下笔错漏百出,谬种流传。不仅无临帖之功,刻意求怪,自诩为艺术,冠之以“现代派”,说白了就是盲求捷径。没有高深的文化造诣,不可能成为名冠古今的大家。名为现代派,实为“江湖体”“野狐禅”,不要说窥得宫室之美,根本就是没入门,更不要说入流了。当下书法界呵祖骂佛,离经叛道者比比皆是。“风骨”缺失,“情操”扫地,值得反思。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不薄今人爱古人”。艺术创作,在守成中有突破,在突破中蕴传承。单纯凭技术的高低很难深人中国书法的内核,不能使书法走向美术化、工艺化的穷途末路。
道听途说,德之弃也。有人说元代杨维桢的书法也是“丑书”。这种“丑”实际上是一种古雅之美,与当代丑书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杨维桢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为人旷达,有晋人遗风。杨维桢书法的价值,有特定时代的因素。有元一代的书法创作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很多人甚至放弃追古,而直接学习赵孟頫,时弊积重难返。元代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很多文人选择归隐避世。杨维桢书法的粗头乱服,点画狼藉,不计工拙,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反映,是内心苦闷情绪和困乱时局的折射,并非刻意的求新求变。乍看之下给人一种偏离正统的怪异之感,“细细品味之后则感觉狂而不乱,虽纵横交错却浑然一体”。杨维桢的这种“丑书”,在当时的书坛反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入古”基础上的“出新”,师承古法,毫无熟媚绰约的“贱态”(傅山语)。
杨维桢的书法,尚属正脉。取法魏晋,盖自《兰亭》稍变而至此,又融入欧阳询的险绝风格,用笔方整厚重,骨力洞达。行笔多以中锋,结字之舒密多继承传统,非主观臆造。章法萦带生动,结字体势恢弘,线条如棉裹铁,性情高逸,自然天成。充满高古奇崛之趣,是当时书坛的一股清流。
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之美”)
越剧《红楼梦2025版》舞台版和电影项目启幕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文化中华·守宝人丨云端守寺三十载
贵州:油菜花海绽春光
中转式旅游:追求“高性价比”与“松弛感”
蛇年寻“蛇”—— 藏在山西博物院里的“蛇”
“冰雪热”遇上“非遗热”,真燃!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理想的都城,秩序的杰作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相关新闻
当代书法家:孔可立作品欣赏
从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后虚怀若谷,,孔可立追求作品的美感和思想纯度,不断挑战书法创作的固有模式,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辛求索之路。其作品旷达飘逸、苍利隽秀、时出天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