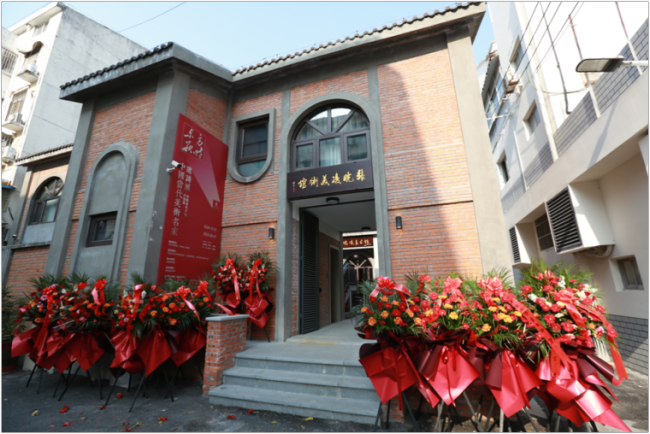“反弹琵琶”形象考:敦煌壁画舞姿形象到底源于何处(6)

莫高窟 五代 第 98 窟舞乐菩萨(反弹琵琶)线描图
关于反弹琵琶能否在旋转中弹奏琵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将琵琶高举到颈背后恐怕是无法反身弹拨的。背后连弹带拨琵琶,即使手拿拨子也不易, 甚至高举双手弹弄都是很难做到的。 琵琶在这里可能只是一种舞蹈表演举起的道具,放下正面怀抱时演奏的乐器。各显神通的随意浮想毕竟是后世人套在古人身上的猜测。
笼统地从年代上说,从盛唐时期兴起的“反弹琵琶” 这种舞蹈形式, 到了中唐仍然流行这种舞姿,只是盛大佛教经变画中一个绘画姿态,那么敦煌的画匠继续关注选择这种唯美的舞蹈动作,很可能有粉本作为描绘大型壁画的来源定本。 宿白先生曾认为“银壶人物中反弹琵琶的图像,多见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在莫高窟所建的洞窟壁画中,如第 112 窟壁南壁东侧观经变相,据此似可推测反弹琵琶的舞姿流行于 8、9 世纪”。
至于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天平年间(724—750)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正是盛唐之物,桿拨上有骑驼胡人左手执琵琶、右手执拨子的艺术形象,被誉为唐代东传日本的西域胡风珍品。 但是胡人边行边弹琵琶而不是“反弹琵琶”的舞蹈动作。 这只是作为同时代可参考的旁证, 故不列入我们深入讨论的范围。
公元前2至公元1世纪犍陀罗 “希腊化的艺术”吸纳汇集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神祇,公元1世纪后佛教雕塑出现,大乘佛教的菩萨就是典型希腊人形象,绾发有髭,鼻梁挺直,公元3—5世纪犍陀罗佛像被大量制造,随着传入中国,逐渐由希腊化男相嬗变为的中国化女相,带有髭须的美男子变为温柔慈善的美女貌。敦煌壁画中有的菩萨还留有八字髭须。
希腊化神话体系中的女妖塞壬, 曾以歌喉魅惑众生,传至印度变成佛教乐神,梵语称之为迦陵频伽,中国称为妙音鸟。人首鸟身的塞壬形象作为佛教中执掌声乐的迦陵频伽,凤身羽毛,或吹笛弄竽或手捧莲花,献于菩萨的面前,一直保留在中国佛教造型艺术中,在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壁画中就有标本。
如果说敦煌莫高窟第112窟壁画主尊阿弥陀佛座前乐舞场面中,反弹琵琶伎乐天是佛及菩萨的侍从,其主要职能是“娱佛”,那么与古希腊祭司用舞蹈在神灵面前“娱神”,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男相变女相,健硕挺拔的男子身躯变成灵动柔姿的轻盈女貌,这超凡脱俗的体态变化就更促使我们思考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有人宣称“反弹琵琶”是中国人独创的乐舞高峰,是中国舞蹈史上民族艺术的绝技,人们形成这样的浮浅印象并不难理解, 因为以前没有见过对比衡量的画像图鉴,现在用中西对比互证的眼光去互鉴、互比、互参,就会发现外来文化入华融合才是真正的高峰。
释读图画与考证的结论:
从上述三个6—9世纪留存的 “反弹琵琶”艺术形象来比较分析,明显可见反弹琵琶图像中最早为开元二十五年(737)贞顺皇后石椁上,整个石椁充溢着外来的西方艺术,其中两名男性胡人反弹琵琶的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拉萨大昭寺吐蕃银壶上的两位男性舞者所呈现的反弹琵琶舞姿,虽具体年代无法确定,但是其展现的中亚艺术风格则是我们判别比较的很好依据。而敦煌无论是盛唐还是中唐时期的反弹琵琶壁画,均显现出 “反弹琵琶”中古“华化”的轨迹,外来样式的图像底本经过宗教性大经变画改造变化,融入佛画散发,千古绝妙的“反弹琵琶”成为中国人审美的“伎乐天”女性形象。
长安、吐蕃、敦煌,都与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脉动有关,“反弹琵琶”绘画作为艺术的互动,由长安胡人矫健修长的男性身姿,到敦煌已经变为柔软丰腴的女性身形;由开元末长安欣赏的宫廷乐舞风貌到敦煌佛窟天上净土中歌舞的景象;由长安京城皇家艺术画师传播到河西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画匠手中,这种美术样式的创造与艺术互相影响的流传过程,千年一见,长足影响,使人们有了重新审视盛唐艺术与外来文明的历史契机,不仅有着时间链条上准确的年轮,而且也是中西合璧跨越交流凤凰涅槃的见证。
(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及网络)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苏轼魂归处为什么是河南?
相关新闻
云冈舞者:飞天婀娜力士雄,西凉乐起动四方
云冈,云中之冈也是飞舞的云冈。云冈石窟,是中国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而形成的伟大艺术成果,在它那雄伟壮丽的石雕群中,有各种风格不同、审美特征各异的舞蹈雕像。
280件乐舞文物见证中西文化交流互鉴
双手各持一支簧管乐器排成V字形,管上有数个小开孔,管底不封口,两支管的哨片同时置于口内。一只中国汉代褐绿釉乐俑,其手持吹奏的却是古希腊原始乐器、现代管乐始祖——阿夫洛斯管。
“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赣州”阳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在日本举行
12月23日,中国江西省赣州市在日本东京举办“知行合一王阳明在赣州”阳明文化对外交流活动,以阳明文化为载体,促进两地文化交流,进一步提升了赣州文化发展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
在日本唱《义勇军进行曲》:松山芭蕾舞团与日本左翼文艺
松山芭蕾舞团在近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声援中国,并不意外:虽然歌曲有着浓厚的抗日背景,但对于主张和中国友好往来、连结反战思想与左翼文艺的松山芭蕾舞团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