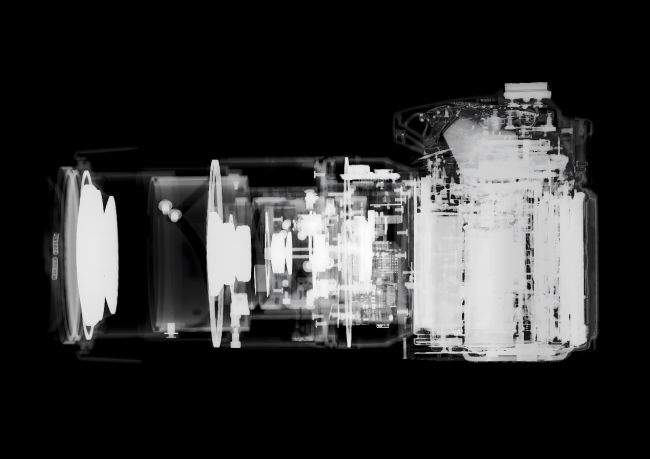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考证与思辨(8)
回到中古时代的西域来看,正如本书已论证的,唐朝在天山北麓地区开拓出一套服务于定居文明生活的军政、民政、路政设施,引入了定居文明因素,而安史之乱后回鹘全盘接收、继承了它,逐步以原有的唐朝城镇为中心定居化,与突厥等游牧部族相比,“回鹘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城市定居生活和农业生活的熟悉和适应。回鹘人是漠北草原帝国中第一个建立大型城市聚落的族群”,并对城市-农耕定居文明因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本书281-282页)。数百年后蒙元时代畏吾儿人成为大受重用的“文明”族群,很可能便是由此打下的根基,那么,不妨也由此推断:也正是这一分化发展,使西州回鹘社会与仍过着草原游牧生活的突厥部落拉开了差距,进而产生了将之视为“化外蛮夷”的蔑视。实际上,先秦时周文化圈的华夏族群在加速发展和整合后,与周边四裔各族逐渐拉开差距,由此在长时段中产生张力,很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机制。
如果是这样,那这就不仅是族群互动中的孤立现象,它本身也呼应、契合本书的结论:“到西州回鹘王朝时代,唐朝遗留下的城镇戍堡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片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群体,天山北麓地区真正展现出相当体量的城市定居文明因素,这不正是丝绸之路天山北道沿线经济发展的明证么?”(283页)
不过,仍须谨慎判断的是,这种经济发展本身,却未必能用来证否当时丝绸之路的衰落,因为当谈到这一命题时,通常所指都是“作为一条国际商路的丝绸之路”,而不是“丝绸之路上城镇的经济状况”。前者的繁荣基于交换领域,而后者却可能来自生产领域,换言之,西州回鹘时代天山北麓的城镇网络,很可能体现出的是经济活动本地化的结果,这与“丝绸之路衰落”并不矛盾,也许根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这种衰落延续至今的最主要特征。(文/维舟)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相关新闻
龟兹壁画:用色彩记录佛经故事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
龟兹壁画中的丝路商旅:看马璧龙王如何救商客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