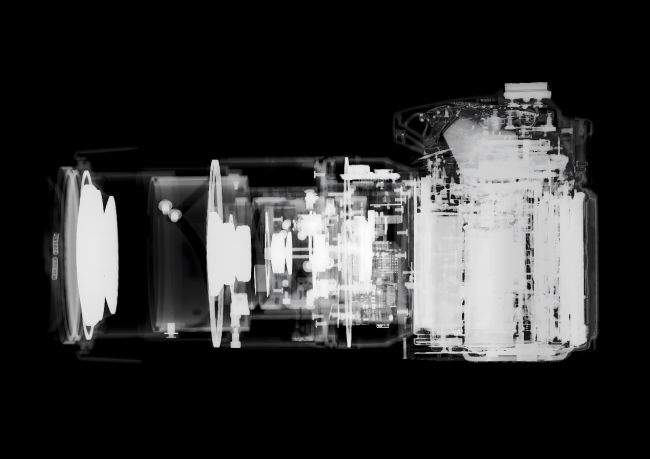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考证与思辨(7)
这种心态不仅限于对异族(如汉人之对“蛮夷戎狄”),常常也针对与自己“同文同种”的人群,甚至正是因为彼此近似,才更知根知底,更有凸显自己有所不同的必要。在近代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兴起之前,这是一种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心态。17世纪末之前,苏格兰高地人被低地同族看作是“无法无天的野蛮人”,其穿褶裙、吹风笛的习俗在当时尚不像后世那样是民族共同的象征,而被视为野蛮落后的标志(《传统的发明》);同样的,地处偏远的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长久以来都被更“文明”的本族蔑视,但近些年来却又反过来被看作是唯一保留着“纯粹”和“原生态”壮族文化象征的人群。人类学者海力波就此在《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中指出:“族群认同绝对不是单纯的工具性博弈手段,而是文化基本认知体系的组成部分,体现出人们对自身、他人、世界的文化想象。”
就此看来,付马在对西州回鹘的族群认同的问题上,正是将之看成了“单纯的工具性博弈手段”,因而才强调“突厥”成为蔑称是双方敌视对立的结果。这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同源的族群随着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拉开差距,自然会产生分化。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开头就指出:“土耳其人”(Turks)这一名称虽然常被欧洲人无差别地用来指称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人,但在其国内却“主要又含有鄙视之意,即系指游牧的土库曼人,或在更晚一个时期,系指安纳托利亚乡村中说土耳其语的粗鲁无知的农民而言的。如果拿它来称呼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上等人,那就无异是一种侮辱”。在这里,“君士坦丁堡的上等人”和“游牧的土库曼人”之间可并没有长期互相敌对的战争。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相关新闻
龟兹壁画:用色彩记录佛经故事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
龟兹壁画中的丝路商旅:看马璧龙王如何救商客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