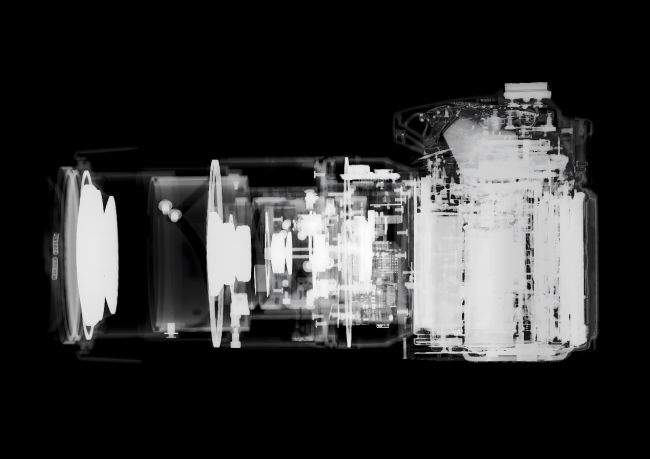今年诺奖在想啥?(4)
尽管人生经历和写作主题会不可避免地让古尔纳被视为一个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但他本人对于后殖民写作是颇有微词的。例如上文提到过的代表作《天堂》。在完成这部小说时,古尔纳表示,过去的后殖民写作很容易成为一个陷阱,因为很多作品都将矛头单单对向了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但其实,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的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也同样可怕。这是在非洲作家中比较罕见的一点。因为非洲作家在现实主题上都比较激进,例如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能够在非洲作家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经历外,也是不仅在小说中批判了殖民者,而是同时描述了非洲部落之间的文化和种族仇恨。
至于开头提到的语言的问题,也曾经有采访者询问过古尔纳,问他是会和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还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站在统一战线上――“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认为可以继续使用英语,并且通过对英语的本土改造实现语言的反殖民功能,而提安哥恰好相反,提安哥认为英语无论如何都只能是统治者的标志,它侵入了价值观、社会行为等一切行为模式。对此,古尔纳回答,这两个阵营都不是他的选择。
古尔纳说,自己不会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理解语言的功能。交流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交流的具体内容要比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重要得多。“我喜欢说我是一个偶然开始写作的人。我在10或11岁的时候没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在英国处于困境中写作,当时我没有想到要说‘我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我知道如何在写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因为那是我阅读的内容。写作和阅读之间的联系是读者和作者建立的整体的文本联系网络。英语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用的,而这是我用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完成的。”
关键词:
光影相伴 共迎新年 2025,电影院见
25-01-03 09:36:57电影
火车“慢”游,一趟集齐沿途风景
24-12-23 10:33:21小兴安岭
河北文旅海外“朋友圈”持续上新
24-11-20 10:30:46河北文旅
逛市集 看演出 赏非遗,去街区赴一场城市休闲游
24-10-21 11:00:29文旅
如何让戏曲“大观园”里“百花绽放”
24-10-15 10:27:20戏曲,剧种
云南白族扎染:“布里生花”展新韵
24-09-29 10:40:50云南白族扎染
2024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闭幕
24-09-25 17:29:18戏曲百戏
《黑神话:悟空》引发海外“西游热”
24-09-13 10:04:26《黑神话:悟空》
巧手制美饰 银辉耀苗乡(匠心)
24-09-10 10:14:41苗族银饰
传承千年文脉 厚植家国情怀
24-09-03 09:53:33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皆是人间好时节 ——感受二十四节气图画之美
24-08-29 09:48:23二十四节气,夏至
先人们是怎么给动物字定型的?
24-08-27 09:32:27动物定型
吉他赋能文旅发展(深观察)
24-08-19 10:29:29吉他文化,文旅
不负青春不负国 点赞巴黎奥运会“00”后中国小将
24-08-12 10:26:28巴黎奥运会赛场
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公布特邀剧目
24-08-08 11:12:56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
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
24-08-05 09:38:00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当“齐天大圣”遇见奥运盛会
24-08-02 09:25:26奥运会,国产动画短片《奔赴热爱》
一线中轴承古通今 一城古韵活态传承
24-07-30 10:58:53北京中轴线
爱此溪山好 阳羡觅东坡(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24-07-26 10:01:20苏东坡主题旅游
中国电影迎来“火热”夏季 多题材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24-07-23 10:13:16中国电影,优秀传统文化
101座博物馆托起“博物馆之城”
24-07-19 10:07:57博物馆之城,太原
谁是史上第一个“吃瓜群众”?
24-07-17 09:24:02夏天,西瓜
在吃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眼光!
24-07-08 11:34:21原始农业
“探秘古蜀文明”展览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24-07-05 10:15:24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星堆
相关新闻
2021-10-08 11:18:00
诺贝尔文学奖
2021-10-09 12:52:11
诺贝尔文学奖
2021-08-30 10:37:09
《雷雨》
2021-07-27 18:15:54
大地艺术展
2021-10-15 11:45:45
河南
2021-10-15 11:40:42
贵州